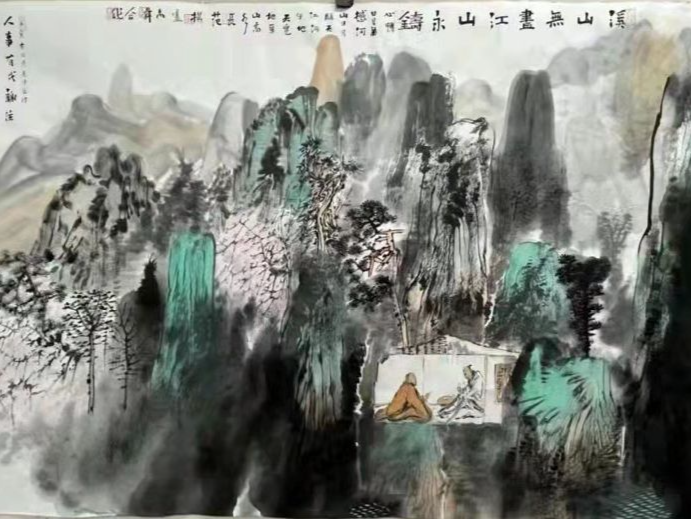无尽藏(第26集)
我再也不曾见过她。时光荏苒,风流云散,故国已成残梦碎影,多少红颜佳人已湮灭不传,多少媚骨芳魂已与草木同腐。物换星移,新朝史官也曾有一些穿凿附会的追记,他们也演绎出诸多有关秦蒻兰的传说,而我深知那皆属无稽之谈。在我的记忆深处,惟有我亲见的那个秦蒻兰。“山有榛兮”,“隰有苓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那空谷幽兰自会与岁月一同老去,那迟暮美人却依然清丽如昔。即使在这风烛残年,我也能时而忆起她那温婉的笑容,忆起她那情思沉郁的风致。我也记得那只虎形豹眼的小猫。我也记起她被小猫咬住脚踝时的尖叫,那叫声中有着怎样的孤寂和欣悦!那只神秘的小猫,牠是那样的温柔可怜,又是那样的威猛狂烈。那琥珀色的眼眸,那如电如炬的目光。当牠优雅地踱步时,牠最先迈出的是哪条腿?
开宝六年的那个秋夜,她以那样一种微笑目送我离去。我背起行囊走出藏书楼。那无尽藏仍是一片火场,那火光也照亮了藏书楼前的梧桐和小径。
那时我拎着灯笼离开那片紫竹林,心里仍在想着藏书楼里发生的怪事:书库里的那卷《太公兵法》已不见踪影。
樊若水先我离开藏书楼。那兵书或许并非是他们要找的秘藏。樊若水或许只是随手拿走它,拿走它或许只因那书名——那轴头上的书名是“录异记”!倘如那是国主所要的秘藏,韩公生前就不会将它摆在通向密室的路口,去往密室的人会轻易地看见它,樊若水去往密室前也会看见它。或许那只是随意的摆置,或许是一种有意的误导。那毕竟是一部千古传说的奇书,即使并非昔日留下的原书,即便只是后世的抄本或刻本,人们也会一眼视其为秘藏。祖本失传,摹本亦是稀世珍品。那卷首确是有“太公兵法”的书名,可它果真是黄石公留给张良的那部奇书么?
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而今的国主不再需要这样的军师了。
或许那是一种有意的暗示。早在三年前的那场夜宴前,韩公就送给我一册《录异记》,而今在这危难之际,这书名又出现在眼前。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未曾用心读这书,此刻就惟有竭力搜索这有限的记忆。
录异记。姜子牙。黄石公。张子房。……
我隐约记得那书上是说木星坠地,其精化身为黄石公,黄石公以兵书授张子房。那是遥远的帝尧时代,那时有五星自天而贯。我蓦然想到书库天幕上的五星,那最明亮的一颗是岁星,而我却不记得那岁星坠往何处了。
越过那片幽暗的湖水,我望见无尽藏那边红光烛天,人影攒动。那些在火光烟雾中晃动的黑影,酷似地狱里的幽灵。我没想到一场火招来了这么多恶鬼!
那些恶鬼忽然发出一片哓呼声,哓呼声伴随着咔嚓咔嚓的断裂声。我望着那些火光中蹦跳的黑影,像是在看一出陌生的鬼戏。
无尽藏的穹顶轰然倒下,那火场溅起一片冲天的火星。
在那火光灼亮的夜空,在那些破絮般的乌云之后,那轮暗淡的圆月正呈现出一片血红色。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红月亮。
我沿湖边小路疾走,有意避开那些或明或暗的院落。我边走边打量着远处的围墙。一旦起获那秘藏,我就当立即逃离这园林。
前方有一道石坊,石坊之后是佛堂,佛堂之后是柳堤。
穿过长长的柳堤,那片菜畦已是隐约可辨了。那菜畦边上有一间茅屋,那是韩公亲手搭建的瓜棚。
我小心地护着灯笼,生怕这灯火被风吹灭。这灯笼就是那宫中的命灯。我要让这灯火亮到我面见国主的那一刻。
风向飘忽不定,烛火也随之摇颤。月光下是奇形怪状的树影,那些树冠枝叶纷披,像是一群山魈野魅在舞动。风声如呼哨般尖厉,又似呜咽般凄怆。我看见雾中闪烁的鬼火,又见树枝如女鬼般披头散发扑来。我的腿脚忽高忽低,头皮也如针扎般炸痛。就在我走下柳堤时,一阵困倦遽然袭来。恍惚间我见这烛火陡然闪亮,火苗瞬息腾高至尺许,像是一只火炬在放大光明。我在这光明中看见一个巨大的头盔,又看见狱中的父亲倚墙而坐,父亲面额焦烂不可辨认。我看见父亲接过一樽毒酒,又见他双手摘下头盔,那双手摘下的却是自己的头颅!
我颓然倒地,顿感万念俱灰。这烛火忽又缩小如前,青焰荧荧在风中摇颤。我在昏沉中望着这微光,忽然便有惊怖的预感。我伸开四肢,如倒毙般趴俯在地。我用额头猛力叩击地面。
一阵剧痛将我震醒,我能感觉到额头流下的血水。
烛火已被鬼风吹灭。我忍泪睁目,昏冥中凄然四顾,忽见前方劈面而来一排鬼影。他们似是从那片垂柳中化形浮现,分明是正朝我走来,我却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
他们无声地走近我,又旋即绕成一个圆圈。我立时落入他们的包围。他们执戈提刀,齐整踏步,上身僵直不动,脚步落地无声。
“大司徒召见林公子——”
僵尸阵中扯起一个长腔。
“请林公子即刻起行——”
大司徒张洎。独揽朝柄的张洎。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口含天宪。
——我是要说与大司徒。
——我也说与大司徒。
威焰熏天的大司徒,他是为王屋山之死而来么?我凭直觉感到,大司徒此刻已身在韩府。王屋山长袖善舞,然终究不过是个舞伎。大司徒深更半夜出行,莫非也是以我为猎物?
我难以摆脱他们的罗网,也难以摆脱那预感所带来的惊惧。我既已断定那秘藏之所在,就不能将他们引向那菜畦。我要面见大司徒,他既是自国主身边来,就定然有我父亲的确讯。假如他确能使我放心,我情愿成为他的猎物。他想要的当然不是我。我会献上他想要的宝物,只望他能确保父亲性命无虞。我本来也是要将那秘藏献与国主,大司徒当能带我进入那深宫。
或许是见我无意抵抗和逃跑,这些青面禁兵倒也显得并不粗暴。他们带我拐上这廊桥,先前我就是从这廊桥逃离湖心岛。
我从未见过这个大司徒张洎,但却熟知其劣迹。潘佑以犯颜直谏得罪,那即是张洎进谗撺唆所致。潘佑初与张洎亲厚,而待觉察张洎为人无操守,便有意与其疏远。张洎遂怀恨构陷,终致潘佑被逼自尽。太学生请愿声讨国贼,张洎便是国贼之首恶。那些请愿书和揭帖上列举张洎大罪者有六:擅权乱政,欺君误国,此其一;卖官鬻爵,敛财害民,此其二。比对其六罪者又有六案,要者一是德昌宫案,二是安丰塘案。
德昌宫本是内府库藏之所,宫使刘承勋监守自盗,金帛泉货多入私家,又以宝货广赂权要。因有大司徒张洎庇护,刘承勋至今仍为德昌宫宫使。刘承勋乃张洎岳丈。本朝那些豪门岳丈均非等闲之辈。当今国主的岳丈是周宗,而周宗本是先主亲信,社稷元老。周宗将自己的二女先后嫁与国主,而其本人则一意聚财,终成金陵首富。国丈爷周宗当年是以大司徒致仕,而这张洎也愿自己被呼作大司徒。大司徒位列三公,司户政地政,有宰相实权。张洎实为清辉殿大学士,亦是枢密院副使。枢密副使掌军机,无奈名衔中有这个“副”字,虽然他比枢密使陈乔更得宠;清辉殿大学士虽有一个“大”字,虽为文臣之极选,但听来却似翰林闲职。张洎愿被呼作大司徒,以此彰显其威势。
安丰塘远在淮南寿州,其塘水溉田数万顷。地产丰沃,民无凶岁。人说国朝覆军丧地自彦贞始,刘彦贞入为神武统军,只因他阿附“五鬼”广遗贿赂,而其财源即是安丰塘。刘彦贞甫任寿州清淮军节度使,即以疏浚城濠为由,大兴工役,决塘水入濠中,于是民田干涸,而征赋益急,民人皆鬻田而去。刘彦贞便择肥沃良田低价买进,复引濠水回流塘中,使安丰塘涨水如初,遂又高价售地。如此买进卖出,岁积巨亿财货。
张洎即是发迹于安丰塘。太学生上书揭发其底细:安丰塘买卖农田的谋划者正是这张洎!那时他在刘彦贞幕帐掌书记。刘彦贞得此妙计暴富,张书记也得获仕进显达的资本。
人说他贪鄙无耻而又好攻人短,而这皆因他自有一套固宠术。笑骂任由他人,我自锐意钻谋。樊若水有国主御赐的金禅杖,这位大司徒又将持何物以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