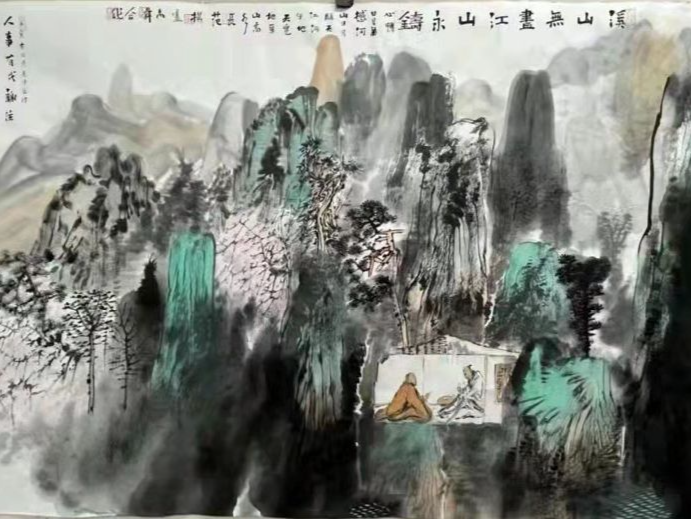无尽藏(第25集)
那藻井下方的浑天仪即是八卦的中央,那浑天仪就是太极之象。在那太极之象的外围,每一组卦象都由六排书柜所构成,每排书柜的断连即是卦象中的爻象。内三排是内卦,外三排是外卦,内外卦之间也有略宽的过道。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
我不再晕头转向。我已勘破这书阵的玄机。我进门时初遇的那个三岔口只在这八卦的外围。凭我有限的《周易》知识,我立时就能判定这八卦迷宫中的方向。八卦对应着八门,这其中只有两个方位是“吉门”:乾位是“开门”,艮位是“生门”。
我进来时经过的那道门就在西北方,西北方是八卦图阵乾位,乾位是“开门”。我从“开门”进来,就当从“生门”出去。
“开门”在西北,“生门”在东北。尽管这圆阵并无直角,我依然能确定“生门”所在的方位。
我跳下书柜,沿着最短的路径拐向“生门”所在的东北方。
眼前的六排书柜构成一个六爻卦象,内卦和外卦皆是一连二断的组合,这正是艮卦的卦象,可此处并无出口。
据此卦象,最上或最外的爻象不该有间断,最外围的这排书柜中间却有一道间隙。一道不易察觉的间隙,似是拼接不严所留的缝隙。然而,旁边的其他书柜却都是严格按卦爻规则设置,绝无这种例外的拼合。
与其他那些书柜相比,这末后一排书柜里书卷尤显稀少。只有几个零散的插架,只有一个青布书函,这函中装有《连山》和《归藏》的麻纸册页。《连山》和《归藏》,此乃比《周易》更古老的两种卜筮书。这书柜的最底层又有一个卷轴,这卷轴的轴头标有“录异记”的书名,我立时就有扑扑的心跳。我慌忙打开这书卷,却见卷首的书名竟是“太公兵法”!这内文显然也会是《太公兵法》的篇章。相传《太公兵法》为姜太公所著兵书,当年张子房遇黄石公得此书,遂助汉高祖刘邦成大业。然而,即便是为张留侯作传的司马迁,也在文末以“可怪”二字为结语,盖因从未有人见过此书的真容。而在韩公的这座藏书楼,在这书柜的最底层,竟然就有这样的一部《太公兵法》!更可怪者,这《太公兵法》的轴头上写的却是“录异记”!这是我要找的秘藏么?是谁将这奇书置放在这明处?而此时此刻,燃眉之急是救出楼上那女人。
这排书柜似也有挪动的痕迹。我试着将其推向一边,就见后边的墙壁上有一道小门。
我手举烛台钻出这道“生门”,一段梯道遽然出现在我眼前,这正是三年前我曾走过的梯道。
这梯道通向阁楼的密室。
“韩熙载毕竟留了甚么?从实招来!”
又是那个沙哑阴沉的男声!
门已反插,我无法推门进去。
“就那书库……那些旧书……”这是秦蒻兰怯弱的颤声。
“咄!生生是死心塌地!老衲有法儿开你口!”
像是猛遭一击,秦蒻兰惨叫一声倒地。接着又有挣扎扭动的声响,又有哧哧的衣袍撕裂声。
“老淫妇张嘴!好生给老衲吃吃!”
我要擂门救她,又怕死在樊若水手里。我将烛台放在一边,一手紧攥匕首。
“好姻缘!”樊若水爆出一声淫笑。
我跑到窗口,从那破碎的缝隙朝里望。
这密室只是方正的一小间。秦蒻兰仰面倒地,樊若水正骑坐在她的胸脯上。僧袍撩起,那阳具直抵着女人的嘴唇。那女人扭动着身体,她在死命地推拒。樊若水甩手猛抽一个耳光。
“还不如实招来!”
“委实是没有……只那些……”
秦蒻兰闭目蹙额,一副不胜隐忍之状。那小猫发出凄哀的叫声。我却看不见牠的身影。那声音似是在高处。
我退后一步思量,若是破窗而入,就有死在他手的危险。父亲托我以重任,我不该这样送死。若是擂门惊动那恶棍,兴许也能救出秦蒻兰。
“恶姻缘!”樊若水一手掐开女人嘴唇,一手欲将那阳具插进去。
我紧握匕首回到门口,我要擂门惊动他。
正在此刻,室内忽然有一声哀嚎,似是杀猪般的嗥叫声,那是樊若水在惨叫。
我猛力擂门,屋里只有樊若水的嘶叫声和扑打声。我又跑到窗口,就看见樊若水正手握短剑追击秦蒻兰。樊若水一手护着裆部,那被咬断的阳具在滴血。秦蒻兰一边躲闪,一边抓起棋盘护身。我后退一步,运足气力踹窗。
就在我踹窗的瞬间,樊若水又有一声惨叫。窗未踹开,我看见那小猫正抓牢樊若水的光头,一只利爪正扎进他的眼窝!
樊若水嚎叫着倒地,小猫也随他一起倒下。樊若水死命地扯开小猫,又一脚踢飞秦蒻兰砸来的棋盘。我踹开窗子跳进去,樊若水迅疾拉开那道门。
他狂乱地挥舞短剑退到门外,护裆的那只手又紧捂着血眼。我的眼前忽然白光一闪,就见那小猫飕地一下跃上柜顶,就在那柜顶的边缘弓身而立。此刻牠居高临下,怒目而视,仿佛是一只悬崖上的猛虎。牠狂乱地甩动尾梢,似是要再次袭击那恶棍。
樊若水猛地带上那道门。我听见他快步逃下那梯道。
即使他手里无剑,我也不想去追赶。太多的节外生枝。太多的耽搁。
秦蒻兰俯地啜泣,泪水簌簌而下。望着这个衣衫凌乱的女人,我的愧疚无以言说。我无意中将这恶棍引到了藏书楼,而她忍辱守护了韩公的珍藏。韩公在天之灵当知,这女人并未辜负他的信托。
小猫默默地踱近主人,静静地蹲在一旁。我望着牠那漂亮的睫毛,正欲伸手抚摸牠的头,牠却突然掉头蹿到那柜底。牠惊魂未定,就在柜底下怔怔地望着我,又哀哀地叫唤一声。
这女人的抽噎倏然而止。她缓缓仰起脸,只看了我一眼,便又垂下头。她的身子斜倚在绣墩上。我在她对面席地坐下。
小猫依然躲在柜底,牠嫌厌地蹭着一只前爪,那爪上黏着脏污的血水。
“只怪我冒失,惹来这祸事……”我期期艾艾地开口。
“只要你找得到……”
“不在无尽藏。”
她吃惊地望着我,眼里依然噙着泪水。
“书库出口有一卷奇书,是你有意摆置么?”
她困惑地缓缓摇头道:“原封未动,都是老爷生前摆置。”
“那我是该仔细看看。还有,诗轴中有个‘梅’字很特别,韩公有否说过……”
她略微一想,又困惑地轻轻摇头。
“那……你可知哪里有一棵梅树么?”
“……这倒是有,阖府就只一棵。”
她拉一下撕破的衣襟微坐起身,眼神也立时有了期待。
“是在那藏园。”
“藏园?我从未听说……”
“就是东篱那菜畦,平日老爷与我说话,就说那菜畦是藏园。我问他何不写块匾,他说只要我心里记着,也别对人讲……”
“那梅树……”
“一株古梅,就在史虚白衣冠冢旁,那里也有条小河的。老爷有时管它叫‘黄河’,有时管它叫‘洛水’……”
“那诗轴的绢地就有河图和洛书!”
“我怎就没看得出……”她浮起一丝淡然的苦笑,这笑意中又有些腼腆。“那你会当快些去,无尽藏失火,想是都奔那边去了。”
“可是你在这……”
“不劳你挂心,我自有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