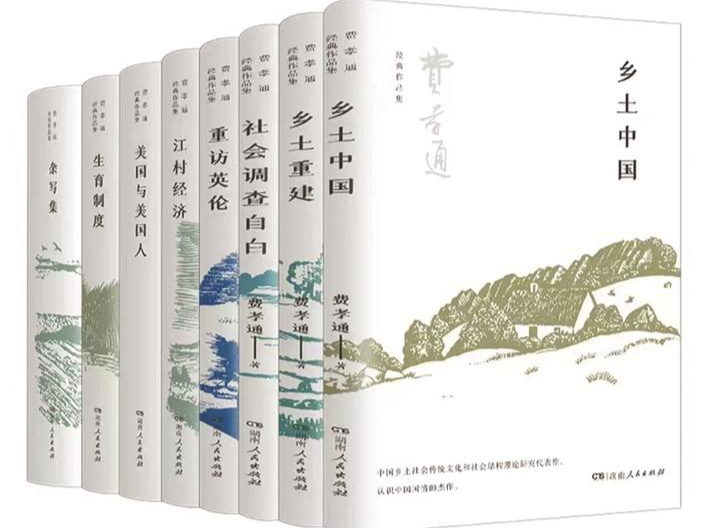“在这个荒诞的时代,我们需要科幻。”作为公认的科幻大师,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作品别具一格:并非硬核科幻,却能洞察人性和科技间最尖锐的矛盾,抵达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恐惧。每个故事都像一则寓言,穿梭在科幻与现实、戏谑与严肃之间,悲观而又不乏对人类未来最真诚的期望。《华氏451》和《火星编年史》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奠定了其科幻小说大师的地位。
雷·布拉德伯里(1920-201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沃基根,今年是他的一百周年诞辰。为纪念布拉德伯里百年诞辰,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推出其经典短篇小说集《图案人》。《华氏451》的大火从这里开始燃烧,《火星编年史》的飞船自此地启航。《图案人》以一个全身遍布可以预知未来的文身图案的神秘男子为线索,牵出18则“黑镜”式天马行空的科幻奇妙物语,每一篇都有诗意而奇诡的想象和出人意料的结局。

《图案人》
(美)雷·布拉德伯里 著
宋怡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6月
故事的关键词是“如果”:如果男人可以给自己量身定制一具机械木偶,晚上出门鬼混时留它在家打掩护,不料它真的爱上了主人之妻?如果某座沉睡的城市一夕苏醒,启动一切科技化感官,对人类展开疯狂的复仇行动?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神父,在布道中却发现真正的上帝并非如你想象的模样?如果一群来自火星的入侵者战战兢兢地登陆地球,才发现人类不过是群沉迷于吃喝玩乐的蠢家伙?……
《图案人》曾于1969年被改编为cult电影,同名系列剧集预计将于2022年由《超感猎杀》导演迈克尔·斯特拉辛斯基搬上荧幕。
自1943年开始专业写作,布拉德伯里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激励了数代读者去幻想、思考和创新。他创作了数百篇短篇小说,出版近五十本书,此外还写了大量的诗歌、随笔、戏剧、电视和电影剧本。他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将现代科幻领入主流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人物”。曾获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卓越成就奖,2004年美国国家艺术奖章和2007年普利策特别褒扬奖。史蒂夫•斯皮尔伯格称他是自己“科幻事业的缪斯”,认为“在科学小说和幻想的世界里他将永生”。

以下内容摘自《图案人》:
前言
序 言:步履不停,只为生命不止
我的侍者朋友,洛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战神广场啤酒屋工作。一天晚上,在为我端上一大杯啤酒时,他向我描述了他的生活。
“我每天要干十到十二小时的活儿,有时是十四小时,”他说,“到了夜里就去跳舞,跳啊,跳啊,一直跳到凌晨四五点钟才上床,一觉睡到上午十点,十一点上班,再继续工作十到十二小时,有时是十五个小时。”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问。
“很简单,”他回答,“睡眠如同死亡,睡着了就像死了一样。所以我们跳舞,为的是远离死亡。我们不想死。”
“你多大了?”我最后问他。
“二十三。”他回答。
“啊,”我感叹着,轻轻握住他的肘弯,“啊。二十三,是吗?”
“二十三,”他微笑着说,“你呢?”
“七十六,”我说,“我也不想死。可是我已经不再是二十三岁了。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在做些什么呢?”
“是啊,”洛朗依旧笑得天真无邪,“凌晨三点你都在做什么?”
“写作。”我终于答道。
“写作!”洛朗惊愕地说,“写作?”
“为了远离死亡,”我说,“跟你一样。”
“我?”
“是的,”此刻我也露出了笑容,“凌晨三点,我写啊,写啊,写个不停!”
“你很幸运,”洛朗说,“你很年轻。”
“目前看来是这样。”说罢,我饮尽杯中的啤酒,回到打字机旁完成一篇故事。
那么,我用以战胜死亡的舞步又是怎样的呢?
在一个又一个故事中,《图案人》藏着一触即发的隐喻。
大多数情况下,我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隐喻正伺伏在那里,等待着从我的视网膜上落向纸面。
人们对大脑内部的活动做出种种理论推测,但它几乎仍是个完全未知的疆域。作家的工作就是“引蛇出洞”,看它如何行事。正如我常说的,“出其不意”就是一切的关键。
以《万花筒》为例。四十六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决定引爆一艘火箭飞船,将船上的宇航员抛入茫茫太空,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便产生了一篇被收入无数选集并在中学和大学礼堂反复上演的故事。全国各地的学生都在课堂上表演这个故事,这让我再次认识到,戏剧无需布景、灯光、服装或音效。只要演员在学校或某人的车库或临街的店铺里说出台词并感受那份激情便足矣。
莎士比亚的无布景舞台仍然是最佳例证。一个明朗的夏日午后,在圣费尔南多山谷看着孩子们表演《万花筒》的茫茫黑暗,我决定创作并上演我自己的版本。如何将跨越百万英里的星际航行压缩在一个宽四十英尺、纵深二十英尺的舞台上,展现在九十九位观众面前呢?尽管放手去做就好。当最后一个人化为燃烧的流星从天空中坠落,在场的人无不眼角泛起泪光。整个时空和那七个人的心跳都被困在台词中,说出台词,便是将他们释放。
“如果……”是我许多故事的关键词。
如果你来到一个遥远的星球,耶稣基督恰好在前一天刚刚离开,你会怎么办?如果他仍然在那里等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由此,产生了《那个人》。
如果你可以在房间里创造一个世界(四十年后,它将被称为首个虚拟现实场景),并把一个家庭引入这个房间,房间的墙壁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一连串噩梦,那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我在我的打字机上建造了这个房间,让我的家人流连其中。未及午时,狮群便从墙壁里跃出,而我的孩子们则在故事的结尾处若无其事地喝茶。
如果一个人能订购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机器木偶呢?如果他自己每晚外出,却把他的复制品留在家中陪伴妻子,会发生什么情况?《牵线木偶公司》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你童年时期钟爱的所有作家都因为作品在地球上被焚毁而躲藏在火星上呢?《流亡者》—三年后,我在《华氏451》中点燃的焚书烈焰便是从这里开始蔓延的。
如果有色人种(在我写作《乾坤逆转》的一九四九年,这是对黑人的称呼)率先登陆火星,定居下来开始新的生活,建好了城镇,他们将如何迎接白人的到来?随后又会发生什么?我用这篇故事来寻找答案。当时,没有一家美国杂志肯买下这个故事。民权运动尚未兴起,冷战已经开始,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正在帕内尔• 托马斯的主持下召开听证会(约瑟夫• 麦卡锡迟些才会登场)。在这样的氛围中,没有哪个编辑愿意与我的黑人移民一起登陆火星。最后,我将《乾坤逆转》交给了《新故事》杂志——那是玛莎• 弗利的儿子戴维在巴黎办的一份杂志。
还有,如果你家后院有一大片废品旧货场,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经不住诱惑,将这些废铜烂铁焊接在一起,去月球旅行?在我十二岁时,距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我家屋后四十英尺就有一个这样的废品旧货场。傍晚时分,我结束这里的月球之旅后,便匆匆赶往两个路口之外的机车“大象坟场”,爬上那些报废的蒸汽机车,在坎卡基、奥斯威戈和遥远的洛克威等小站短暂停靠。在旧货场的火箭飞船和早已被人遗忘的机车之间,我从来无暇回家。《火箭》便是这段经历的产物。
这些“如果”在我的头脑中来回反弹。
换言之,我的大脑左半球(如果真有所谓左半球)提出假设,大脑右半球(如果真有所谓右半球)给出结论。
如果右脑空空如也全无反应,左脑再怎么假设也是枉然。我幸运地拥有某种禀赋。上帝、宇宙秩序、生命力,无论哪个在起作用,都让我的右脑像接球手一样稳稳接住从左外场越过本垒板疾速而至的一切来球。左边的半球似乎就在明处,右边的半球则始终保持神秘,激起你将它引到明地里来的欲望。
如同沟通灵界的降神会,打字机、电脑、笔和纸就是我的工具,用来捉住那些即将消失在空中的鬼魂。
说正经的,我父亲会这样抱怨。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的是,创作的过程很像用那种笨重的老式相机照相,你钻到黑色布罩下面,在黑暗中捕捉影像。拍摄对象也许不会老老实实地站着不动。光线也许太强或太弱。你只能在暗中摸索,但是动作要快,以期得到一张可以显影的快照。
本书中的故事就是一些冲洗出来的快照,它们在黎明时分被唤醒,在早餐时逐渐构思成形,到了中午便会最终确定。上午十点,所有的故事尚无定论;而就在午餐过后,或是啜饮着浓酒与淡咖啡的下午四点,它们全都有了各自或喜或悲的结局。
勇敢去爱,正如一首老歌里唱的。
或者借用梅尔• 布鲁克斯在《十二把椅子》中的歌词:
抱最好的希望,
做最坏的打算,
你可以成为托尔斯泰
或是范尼• 赫斯特。
我希望成为赫伯特• 乔治• 威尔斯,或是与儒勒• 凡尔纳为伴。当我在二者之间开辟出一块生存空间时,我感到欣喜若狂。
最后再回到本文的开头。我在巴黎当侍者的朋友,洛朗,整夜跳舞,跳舞,舞步不停。
我的旋律和曲目就在这里。它们填满了我的岁月,那些拒绝死亡的岁月。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作,写作,在正午时分或凌晨三点笔耕不辍。
为了生命不止。
雷• 布拉德伯里
《城 市》
这座城市等待了两万年。
斗转星移,田野里的花儿开了又谢,城市在等待;地上的河流潮涨潮歇,化为埃壤,城市在等待。曾经年少轻狂的风已变得老成持重,曾经被疾风吹皱又揉碎的白云如今不受打扰地在天空中悠然飘荡,城市依然在等待。
城市里的千窗万户和黑曜岩墙壁在等待,城市里参天的楼塔和旗帜不再飘扬的角楼在等待。城里的街道上了无人迹,没有撒落一片纸屑,房屋的门钮无人触碰,没有印上一枚指纹。城市所在的行星在轨道上围绕着一颗蓝白色恒星转动,季节在冰火之间往复流转,原野绿了,夏天的草地黄了,城市在等待。
时间来到第两万个年头的一个夏日午后,城市终于结束了等待。
天空中出现了一艘火箭。
火箭飞了过去,又调头飞回来,降落在距离黑曜岩城墙五十码的页岩草甸上。
几只穿靴子的脚踏上了稀疏的草地,火箭里的人在喊着火箭外的人。
“准备好了吗?”
“好了,全体注意!向城里进发。詹森,你跟哈钦森打前哨。保持警惕。”
城市张开隐藏在黑色墙壁中的鼻孔,位于城市深处的一个吸风口通过管道吸入大量空气,经过蓟形过滤器和灰尘收集器处理后,进入一组银光闪闪、极其精密的线圈和网络中。空气被不断地大量吸入,草地上的各种气味随着阵阵暖风被输送到城市里。
“火的味道,陨石和铁水的味道。来了一艘外星飞船。黄铜的味道,火药、硫磺和火箭燃料燃烧的味道。”
这些信息记录在纸带上,经由链轮转动送入进纸口,再由黄色的齿轮组送往其他机器做进一步处理。
咔嚓—嚓—嚓—嚓。
一台计算器打着节拍。五,六,七,八,九。一共九个人!打字机将这条信息即时打印在纸带上,纸带倏地一闪就不见了。
咔嗒嗒—咔—嚓—嚓。
城市等待着他们柔软的橡胶靴底落下。
城市巨大的鼻孔再次张大。
黄油的味道。从这伙悄悄靠近的人身上释放到空气中的淡淡气味随风飘送到城市的鼻孔里,在那里被分解为牛奶、奶酪、冰淇淋、黄油等记忆中的乳制品的味道。
咔嗒—咔嗒。
“大家要当心!”
“琼斯,把你的枪拿好。不要掉以轻心。”
“这是座空城,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可说不准。”
在这吵闹的对话声中,耳朵苏醒了。在倾听风的低语、树叶飘落和融雪时节嫩草初生的平静中度过了许多个世纪,如今耳朵为自己涂上润滑油,绷紧了巨大的耳鼓,入侵者的心跳声敲打在上面就像是蚊蚋的翅膀在振动。耳朵认真地倾听着各种响动,鼻子努力地收集着一切气味。
闯入者流下紧张的汗水。他们的腋下出现了成片的汗渍,握枪的手心里也是汗津津的。
鼻子反复抽吸辨别着这股气味,好似一位鉴赏家在细品一杯陈年佳酿。
嘁—嘁—嚓—咔嚓。
信息被记录在平行检验带上。汗液;氯化物含量百分比;硫酸盐含量;还有尿素氮、氨态氮,由此得出肌酐、糖和乳酸指数。分析完毕!
铃声响起,初步计算结果出炉。
鼻子将经过检测的空气轻轻呼出。耳朵倾听着人们的对话。
“我认为咱们应该回飞船上去,船长。”
“这里由我指挥,史密斯先生!”
“是,长官。”
“喂,前边的!哨兵!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长官。看来这里已经荒废很长时间了!”
“听见了吗,史密斯?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我不喜欢这儿,原因我也说不上来。你可曾觉得某个地方似曾相识?这座城市就让我感觉过于熟悉了。”
“胡说。这个星系距离地球数十亿英里之遥,咱们根本不可能来过。而且咱们的飞船是第一艘能够跨越光年的飞船。”
“可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长官。我认为咱们应该尽早离开。”
众人的脚步犹豫了。凝滞的空气中只有这些闯入者的呼吸声。
听到这里,耳朵加紧行动起来。轴轮旋转着,晶亮的液体汇成细流流过阀门和鼓风机。根据一个又一个分子式,一种又一种化合物被合成出来。片刻之后,在耳朵和鼻子的号令下,气味清新的蒸汽通过墙壁上巨大的洞眼吹向闯入者的鼻端。
“闻到了吗,史密斯?啊——青草。还有比这更好的味道吗?天哪,我真想站在这儿闻个够。”
肉眼看不见的叶绿素分子拂过停下脚步的几个人身旁。
“啊——!”
脚步声继续向前。
“没有任何异常,是吧,史密斯?快走啦!”
耳朵和鼻子稍稍放松了一瞬。反制行动成功了。卒子们继续往前走了。
城市阴郁的眼睛从雾霭中露了出来。
“船长,看那些窗户!”
“什么?”
“那些房子的窗户!我看见它们动了!”
“我没看见。”
“它们动了,颜色也变了,由暗变亮了。”
“在我看来,那就是些普普通通的方窗。”
模糊的物体变得清晰。在城市的机械沟壑中,涂满润滑油的机轴重重地落下,平衡轮浸入绿色的油藏。窗框屈伸着,窗户闪着光。
在下面的街道上走着两个侦察兵,另外七个人跟在后面,与他们保持着安全距离。他们身穿白色制服,眼睛湛蓝,脸色红得像是刚挨过一记耳光。他们手持金属武器,用后腿直立行走。他们脚上穿着靴子。他们是男性,眼耳口鼻一应俱全。
窗户抖动着,慢慢变薄。它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扩大了,就像无数只眼睛的虹膜。
“我跟你说,船长,那些窗户有问题!”
“别胡说了。”
“我要回去了,长官。”
“你说什么?”
“我要回飞船上。”
“史密斯!”
“我可不想掉到什么陷阱里去!”
“你被一座空城给吓跑了?”
其他人哄笑起来,笑声中带着不安。
“你们就笑个够吧!”
他们脚下的街道由石块铺就,每个石块宽三英寸,长六英寸。街道微微向下一沉,幅度微小得令人无法察觉。它在称量这些入侵者的体重。
在一间地下机房里,红色指针指向一个数字:一百七十八磅……二百一十,一百五十四,二百零一,一百九十八——每个人的体重都被登记在册,记录由卷轴传送到一处相邻的黑暗之中。
这时城市完全苏醒了!
通风口吐纳着空气。入侵者嘴里喷出的烟草味,他们手上残留的药用软皂味,就连他们的眼球都带有一种极细微的气味——城市检测出这些气味,并将信息层层汇总。窗户清澈明亮,耳鼓越绷越紧——城市的所有感官就像一场无形的降雪笼罩着整个空间,计数着入侵者的呼吸和心跳,听着,看着,辨别着。
街道就像城市的舌头。这伙人每走一步,他们足底的味道就会通过铺路石上的气孔传到下方的石蕊试纸上。这份暗中收集的化学成分数据和其他不断累积的数据汇合在一起,等候着那些呼呼作响的转轮和辐条给出最终的计算结果。
脚步声。有人在奔跑。
“回来!史密斯!”
“我才不呢,去你的吧!”
“弟兄们,抓住他!”
脚步声越加迅疾。
最后一项测试。在听觉、视觉、味觉、触觉轮番上阵,并对这些人进行了测量比对之后,城市还有最后一项任务需要完成。
路面上张开了一口陷阱。正在奔跑的船长消失在陷阱中,谁也没有发现。
他被倒吊起来,一把剃刀划过他的咽喉,另一把剃刀剖开他的胸膛,他的内脏被迅速掏空,尸体被平摊在街道下方一间密室的台子上。巨大的水晶显微镜审视着红色的肌肉纤维,没有身体的手指探查着仍在跳动的心脏。他被割开的皮肤被固定在台子上,几只手敏捷地更换着他身体的组件,如同一个奇特的快棋手操纵着红色的棋子。
上方的街道上,史密斯在前面边跑边喊,其他人在后面边喊边追。而在下方的密室中,船长的血流进烧杯,经过摇动、搅拌,被涂在载玻片上送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和计数。他的体温被测量出来,他的心脏被切成十七块,肝脏和肾脏被熟练地一分为二。他的颅腔被钻开,脑子被取出,神经像配电板上杂乱的电线一样被拽出来。他的肌肉被牵拉着测量弹性。与此同时,在城市地下的电气室里,城市的大脑终于得出了最后的结论,所有的机器此时全部戛然而止。
最后的结论——
这些入侵者是人类。他们来自一颗遥远的行星,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形状,他们走动时有特殊的步态,他们携带武器,会思考,会争斗,还有他们的心脏和所有其他器官,这一切都与很久以前留下来的记载相符。
在密室上方,这群人正朝火箭的方向跑去。
史密斯跑在最前面。
最后的结论——
这些人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守候了两万年就是为了再见到他们,我们等待着向他们复仇。所有的特征都吻合。这些人来自一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两万年前,他们向陶伦星球宣战,对我们进行奴役,并用一场大瘟疫毁灭了我们的世界。他们将我们的世界洗劫一空后,便去往另一个星系居住,以逃避他们带来的那场瘟疫。他们早已忘记了那个年代和那场战争,忘记了我们。但,我们可从来没忘记过他们。他们是我们的仇人。这一点确凿无疑。漫长的等待今天终于结束了。
“史密斯,快回来!”
必须争分夺秒。船长被掏空的尸体摊开在红色的台面上,又有几只手紧张地忙碌了起来。它们在他体内植入铜、银、铝、橡胶和丝绸等材料制成的五脏六腑;一张黄金蛛网嵌入了他的皮下;一颗发出蜂鸣声、闪着蓝色电火花的铂金大脑被放入他的颅腔,通过电线与躯干四肢相连。一切就位之后,他的身体立刻被缝合,脖颈、咽喉和头颅等处的创口全部用蜡封好——现在的他完好无损,焕然一新。
船长坐起来,活动了一下双臂。
“站住!”
船长重新出现在街道上,端起枪扣动了扳机。
史密斯心脏中弹,摔倒在地。
其他人转身看着船长。
船长跑到他们身边。
“这个笨蛋,居然害怕一座空城!”
众人看了看脚下史密斯的尸体。
又回头注视着船长,眼睛先是瞪大,继而又眯缝起来。
“听着,”船长开口了,“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们说。”
到目前为止,城市已经动用了各种手段,此刻,它准备使出最后的杀手锏——语言的力量。它的话语不是出自高墙广厦的愤怒与敌意,也没有借助鹅卵石街道和机械堡垒的威严厚重,而是由一个人平静地娓娓道来。
“我不是你们的船长,”他说,“我也不是人类。”
众人惊讶地倒退几步。
“我是这座城市。”他微笑着说。
“我已经守候了两百个世纪,”他接着说,“我在等待那些人的后代回到这里。”
“船长,长官!”
“先听我说下去。谁建造了我——这座城市?建造我的人早已过世,他们是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古老种族。地球人听任他们死于一种可怕的疾病,一种无药可医的麻风病。这个古老的种族期望有朝一日地球人会再度归来,于是便在这颗‘黑暗行星’上,在‘世纪之海’的岸边、‘死亡山脉’的脚下,建造了这座城市,并为它命名‘复仇之城’——这些名字多么富有诗意。这座城市是一杆秤,一剂石蕊试剂,一根天线,用来检测所有到访此地的星际旅客。两万年来,仅有另外两艘火箭曾在此登陆。一艘来自一个叫做‘恩特’的遥远星系,在对船员们进行检查称重之后,发现与记录不符,于是便将他们毫发无伤地放走了。第二艘火箭也是同样的情形。可是今天,你们终于来了!对你们的复仇将严格贯彻到每一个细节。城市的建造者早在两万年前就已死去,但他们留下了这座城,迎接你们的到来。”
“船长,长官,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也许你应该回飞船上去。”
城市在震动。
路面裂开了,船员们尖叫着掉了下去。在下坠的途中,他们看见剃刀闪着寒光迎面而来。
过了不久,响起了点名的声音。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