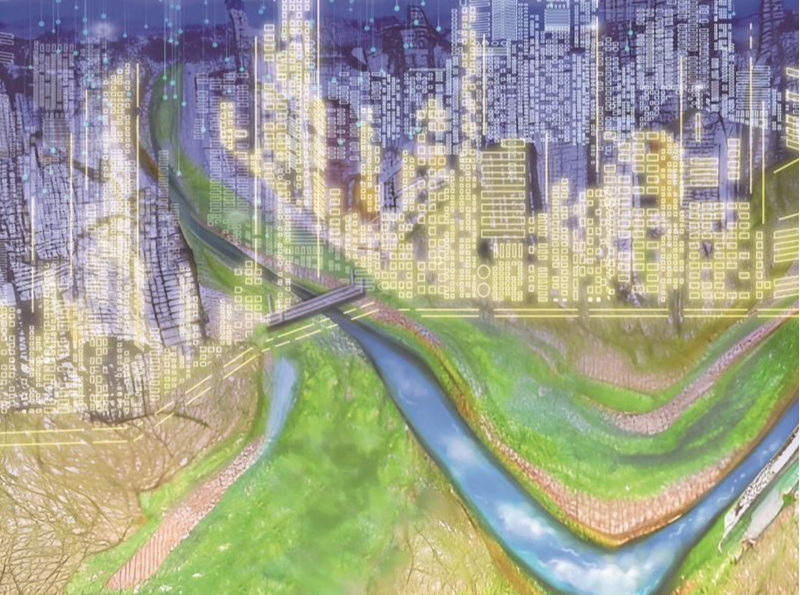■张琦

文本心灵
十年前,任凭谁也无法预料,茨威格的读者能在戏剧舞台上,与小说中的陌生女人相遇——这估计是相当一部分人梦寐以求的文学愿望,类似回到“黄金时代”。完成采访后,我重读原著,仍震撼和失语,她身患重病、自知将死,又如何下了决心,写这封厚实、热忱的书信,寄往暗恋对象无意而随心的余光之中。
至少这悲伤,经年累月,以至于彻骨。书信,却分外安宁和小心——“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张玉书译,下同)。娓娓道来,像诉说无关紧要的事件或情绪,比如远方天气变冷、草叶枯黄。可是,她的爱和命运,自十三岁遇见他起,便形成本质联结,两者甚至成为一体。我觉得,唯独如此,临终前为他写信,才相当自然、完整、妥帖。
想起了这句诗:“你可以放心地/用雪来款待我”(黄灿然译)。保罗·策兰或徒步于一个炎热无望的夏天,桑树叶子年轻。
但,不可能没有恨。与小说相区别,在孟京辉的戏里,陌生女人选择自尽——“既然我对你来说虽生犹死,我又何必不乐于死去。”其中透示出的剧烈和决绝,隐藏在文本背面。实际上,正是书信中时间的遗憾、命运的无奈,打动了这位著名的话剧导演。他认为,这是一种“疯狂的价值”和“遗憾的美感”,和道德、和事实无关。
孟京辉觉得,改编文学作品是一种能量交锋,茨威格的东西强大,首先要磨平想法,要返回小说,基于此,才可动用个人美学,去选择美术、选择媒介、选择音乐影像和视觉,从而涉入文本心灵。
作为唯一演员,黄湘丽接住了导演的观念,她也不满足简单描摹,不愿意亦步亦趋,而是沿着文本延展,将复杂情绪具象化。比如,通过眼神中一丝掠过的性感、眉毛一簇的愤怒感,建立一种想象力,进入晕眩,进入恍惚,如天线召唤闪电,如白裙引渡情欲,于是,不再只是表达爱情。
我看戏看得迟,最后一幕,性感的陌生女人,举起了刀。红酒瓶倒下,刺眼的红顺着坡度缓缓流下,前方的白玫瑰,惹得观众眼睛生疼。孟京辉感觉到,这部戏“离小说越来越远,但精神上却离茨威格越来越近”。而黄湘丽是独立的——“她站在舞台上的一瞬间,她以一种什么样的目光来面对观众,我觉得就是全部。”她是独角戏的“革命者”。
6月底,《狐狸天使》来到深圳,为腾出时间采访,黄湘丽提前来到后台准备。她长裙素绿、淡妆不遮雀斑、举手投足溢出艺术家的灵气。她言语松弛,温和应对我的紧张提问,在我仅用十分钟读完提纲问题、并经几次深呼吸后,属于她的漫谈便真的开始了。

▲黄湘丽上台,像一颗跃动的星星,像驳杂夜空中的坐标,像午夜漫游时的路灯。
动物凶猛
实际上,2013年春天,这部戏立项后,剧组也并不确定是否真的能演。对于独角戏,孟京辉没排过,也没有演员熟悉,何况是改编“心灵捕手”茨威格的小说。恰好,赶上“恋爱的犀牛”剧组休息,饰演“明明”的黄湘丽有了空闲。孟京辉疯狂,让她自己先读小说感受,自行排练。
黄湘丽从没演过独角戏,就这样应了建议,开始独自创作。花了一个月排了第一版,被否定,再用几天又排一版,被否定。直到第三版,导演仍觉得没有抓住剧本核心、都不可用。他沉默良久,决心以音乐作为途径,要求黄湘丽自编自唱自演,逼迫她达到个人极限。即使她未受过作曲训练,只是乐感很好。
第一反应是自我怀疑,但既然被逼到绝境,就等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反而,在安全状态下,行动定要受阻。黄湘丽喜欢和自己较劲,导演一番激将之后,她几天不出门、抱着吉他坐在沙发上,用仅会的四个和弦,憋了三个小时,创作了第一首歌。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七天写出三首歌,填了词唱给导演听。
“可以重新开始排练了。”孟京辉听完之后,抽了半天烟。仍是疯狂,在排练现场,导演、戏剧构作和演员三人,各自手持茨威格短篇小说集共读——“她和W先生面对面吃了早餐”——那不如做个早餐,孟京辉继而想到,还有柠檬、牛排、橄榄油,迅速让人买来厨具,黄湘丽开始煎鸡蛋。
7月,排练场被装修成现代化的整体厨房,大多数时间,只有黄湘丽一个人,手拿菜刀做菜;8月,她被派去爱丁堡艺术节,十天看了三十部戏,学习各种奇奇怪怪的表演方式;9月,奥地利编舞大师多丽丝来为她指导形体,她变成了将自己扔在地上的一块猪肉、将自己不断打碎的一片玻璃——
身体变得透明,并勇敢发出动物的声音。
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她所有表演技能、所有媒介实验,都专注在如何与“陌生女人”建立心灵联系。她犹如海绵和海胆,“浑身张开”,吸收陌生女人极致的真诚、偏执。音乐、菜肴、玫瑰,浪漫又日常的意象,在孟京辉的舞台萌动和生长。她说,导演像魔法师,开启自己身上的多扇窗户。我想到,独角戏是锁孔,而她自己是魔法本身。
10月,最后一次彩排,黄湘丽仍被导演批评。因为临时改词,又不停错、不停错。在化妆间,离首演还有四十分钟,因是独角戏,其他演员都不在候场,只有她和化妆师两个人,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帷幕开启,一身白色连衣裙,四肢柔韧颀长。她登上舞台,踱步、低语,像展开书信的前奏。就在回头这一瞬间,看见观众的时候,她的忐忑和焦灼,纷纷烟消云散了。她是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即将面临初恋之海的青涩少女。短发雀跃着,迎接这些。

▲最近这几年,黄湘丽几乎不再知道,是自己选择了戏剧,还是戏剧选择了自己。
戏剧灵韵
时隔多年,黄湘丽仍能想起,十八岁考取中央戏剧学院后,第一次走进“黑匣子”观看《小妇人》的震惊。北京偌大,无意而短暂的下午很多,唯独在这几个小时,她理清了对戏剧的误解和迷惘,解决了入学以来的种种不适应。
本来谈不上多热爱表演,但这一次,她惊觉,原来,戏剧可以让观众随着演员一起呼吸、一起掉眼泪,这是真实、伟大的。师哥师姐们在舞台上举手投足间的投入、观众们将台阶和过道塞满的炙热,牵动着她的神经。她自此相信,表演并非之前所认为的,充满虚构和假装。她决意学好表演,把这股热情传递给观众。她坚持早起出晨工,研读繁重的理论和剧本。到了大三,排演《雷雨》,黄湘丽出演五四风潮下的青年女性繁漪,其演技已经让老师赞不绝口。
下了决心,便孤注一掷、不留退路,黄湘丽向来如此。自幼不甘于家乡岳阳的波澜不惊,早想去“更大的世界”。1997年,仅十三岁,便鼓足勇气告别家人,独自去北京学舞,有同辈四五岁入门,她付出数倍努力,忍受训练疼痛,顺利被东方歌舞团录取。两年后,为了延长艺术生涯、一直留在舞台,又辞去光鲜的舞蹈工作,备考中戏表演专业。新的转折是,2003年入学,读书、看戏、拿国家奖学金、逛石景山公园,都是正经事。她将读大学视为一种执念。
另一面,她恋旧、慢热、不太喜欢互联网,刚毕业时,在电视剧剧组结交了朋友,又因杀青解散而分别,她为此好伤心。而戏剧艺术,新鲜而恒久,甚至需要奋不顾身、贯穿一生。孟京辉成立新剧团,她收到消息后欣然前往,并经过了层层选拔,成为一名全职话剧演员。
2008年,北京蜂巢剧场,黄湘丽首次登上戏剧舞台,便是参演《恋爱的犀牛》,2012年,接演女主角明明。她对我说,这部戏演得最早、演了很久,融入了血液和身体。我想,黄湘丽同样构成了明明的一部分,融入其血液和身体,于是柔媚暗涌。我无缘再看,遍寻视频,明明冷艳又甜美,“像一颗柠檬”。
为什么要做戏剧,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剧团签约之前,导演的理想主义式发问,牵引出黄湘丽无数个磨人、骄傲又飞扬的戏剧之夜。也曾遭遇过身体不适,躺一整个白天,晚上硬上舞台、腿都在打颤,但演完后觉得好了大半,她开心,下场时觉得自己是英雄:“演戏是治病的”。
最近这几年,黄湘丽几乎不再知道,是自己选择了戏剧,还是戏剧选择了自己。总之是命中注定,是孤注一掷的人生指向。她说,她外在随和、很好接触,但内心挺拧,不想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只做自己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孟京辉偏爱她如同精灵,灵动而诗意,同时敢于冒险,将灵魂向观众全部袒露。
这样的黄湘丽,没有理由演不出独特的“陌生女人”。
舞台上,告别青涩之后,她是魅惑和危险的混合体。敞开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一件件脱下内衣,将自己蒙在被单里——那纷纷的情欲,通过手持DV投射到屏幕。随之是冬天般荡到谷底,直至秋日,万物萧瑟。陌生女人短发凌厉,带来喘息、带来风,带来四季轮回,“一切都是特别美妙”。

▲舞台上,告别青涩之后,她是魅惑和危险的混合体。
独角琴声
到现在为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已演出近千场,黄湘丽参演的戏接近三千场,像劳动模范。实现如此密集的频率,似乎难免需要重复机械的工作状态。但与表象相反——舞台上的重复,令黄湘丽厌恶。不断创造,始终是她最为着迷的东西。
黄湘丽热爱音乐、黑白电影和文学,欣赏娄烨、推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象力、想与瓦林科夫斯基喝一杯。和木马乐队合作的《危险游戏》,她选了莎士比亚长诗作为一段词,曼陀铃和小提琴成了烘托,我伴随海浪声踏入森林深处,这来自音乐的伟力。
在孟京辉刺激下,属于她的专长和日常兴致,强烈融进戏剧表演,多种媒介在舞台上跳跃和融合。她问我,这是什么感觉,我不假思索:相当沉浸,她说,触及心灵。我回过头再听吉他,初遇作家时弹拨清亮简洁,然后是虚弱和刺耳的泣诉,嘈嘈切切,又想起茨威格几个段落,这仍来自音乐伟力。
况且,黄湘丽的创造,不只是音乐、影像等媒介运用。根本上,她觉得,戏剧创作是想象一个世界:最初,依靠茨威格,接近和成为角色,随着时间和经验累积,对小说的理解自然发生变化,于是,文本背后隐藏的情感日益显现。她所做的,是迎接变化、是专注感受和诠释。十年过去,她感慨,不一定再临时回到文本,但原著的能量,确实取之不尽。
黄湘丽也接受创作困难的发生,接受创作力的受困。面临瓶颈,她会做点调整,比如停下来用心生活。因为真正的灵感,藏在日常之中。比如,无奈取消的约会、无故失联的朋友、不期而遇的书籍。比如,某天飘然而至的云。她已经知道,这些困境时刻,都会过去,喜欢便不会复杂。
2020年初,疫情开始,演出暂停,黄湘丽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师和玛格丽特》和《悉达多》,用钢琴写新歌,也排练新戏。重归舞台后,她更从容地与不确定性相处,更珍惜每一场演出,更清楚要坚决做的事。在娄烨导演的《兰心大剧院》中,她出演的白云裳,认定了方向就走下去,即便身处战争。她说,她会一直站在话剧舞台上,一直演到老。
如今,她是《你好,忧愁》中灵动的法国女孩、《九又二分之一爱情》中痛苦绝望的理发师、《狐狸天使》中难以捉摸的百变精灵。身为艺术家,她也开个人演唱会,办个人摄影展,把翻转黑白照片手工上色,做肖像作品。前不久,参加南京第一届1701节。孟京辉评价,因为黄湘丽可以演才做独角戏。
简单吃点东西、化妆,等待灯光亮起。她回忆,有次上台,有的光线照着灰尘,有的直冲眼睛,于是台下变得一片漆黑。她恍惚,剧场里的人好像全部消失了,呼吸声很轻。一种由衷的、被信任的感动袭来,她独自弹琴,款待大家潜入书信里的世界。

▲陌生女人短发凌厉,带来喘息、带来风,带来四季轮回,“一切都是特别美妙”。
植物学家
到家已是深夜。黄湘丽渐渐平静,从角色中走出,这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再睡够十小时后,一切重新开始:健康饮食,减少社交,积蓄能量。傍晚来剧场,简单吃点东西、化妆,等待灯光亮起。
这些年,演独角戏后,生活范围更小,但她特别喜欢这种状况。如果当天没有演出,她首先选择独处——起床后晒太阳、安静听音乐,下午读书,黄昏时听黑胶唱片、跟着节奏跳舞,到了晚上看一部电影。天气适宜,也愿意外出约见朋友,散步、喝咖啡。私下里,她特别热情,戏里戏外,漫不经心下厨,凭着直觉放油和撒调料,盛出来却异常好吃。
疫情时,有段休息期,长达五六周没有演出。第一周,失眠和昏睡,第二周,跑去游客罕至的草原深处,结识当地牧民野游。她坐在绵延的草地上,远方树木零星,牛羊在侧,“天蓝得像一个秘密”。
在家里,她也经常蹲在地上,看着自己养的上百种植物出神。包括八十多盆多肉、二十多盆绿植,还有搜集的一些奇异植物。我猜测,大概是按照造型、气味、长势和个人情绪等等。普通一点的,像龟背竹,还有海芋、密叶猴耳环和不可食用的菠萝、味道浓郁的凤梨。不普通的,像鱼骨令箭,养了好几年,据她说造型极为奇异。
关于如何做一名植物学家,我也深感兴趣,甚至想到几本植物类小说,提供给黄湘丽参考。我们眼睛发亮,她说,和植物待一起很舒服,因为确实不需要说话,而且可以互换能量。何时渴、何时少了光照、何时吹些新鲜的风,都是和植物沟通所得。她感到,一种植物是一种能量。我说,那么,上百种植物就是上百种能量,家里富饶。
不过,大部分植物,都历经萌芽、生长、成熟和衰败的一生,简单纯粹、富有执念,只是或快或慢、或紧凑或舒展之类的。她擅长察觉其中美妙,喜欢与之相处,并身体力行。十三岁在岳阳,家人送她一个人去北京。火车站台,其他小朋友在哭,她不哭,期待眼前铺开的、更大的世界。
采访那晚,是《狐狸天使》的演出。我订的位置靠后,但这舞台的新世界缩而不减。黄湘丽上台,像一颗跃动的星星,像驳杂夜空中的坐标,像午夜漫游时的路灯。意志和情绪又被牵走,有一阵,我闭上眼,回忆起了茨威格一部小说的结尾。
“她飘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
版权声明:
本专栏刊载的所有内容,版权或许可使用权均属晶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复制或改动,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如需转载或使用,请联系晶报官方微信公号(jingbaosz)获得授权。
来源:晶报APP
编辑: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