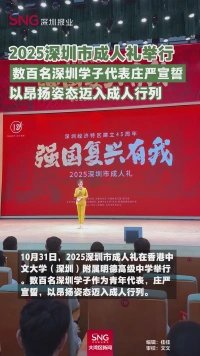中国人究竟应该建造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站?
29年前载人航天工程立项的那个9月,空间站作为工程“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还只是远景与目标。今天,它已经在地球之上日新月异地开枝生叶。
过去几天里,神舟十二号飞船携三名航天员返回地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升空。等到神舟十三号上天,核心舱和靠泊飞船将共同呈现为一个小型的T字构型。明年两个实验舱发射升空后,整个中国空间站就是一个大写的T字型了。

大道有形,积厚成器。天宫家园的一砖一瓦,皆承载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思想与使命。今天,我们来聊聊蕴含在中国空间站T字构型之中的科学、技术与工程原理。


▲2021年7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拍摄的航天员刘伯明在舱外工作场面。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仍以联盟飞船为例,三舱选择“轨-返-推”还是“返-轨-推”构型?考虑飞船在地面和低空的逃逸需求,返回舱布局在船箭组合体的最顶端是有利的,即“返-轨-推”。但是,返回舱要保证航天员能够进入轨道舱、且能够与空间站对接,就得在两端开门。返回大底上若开门,在保证密封及返回防热等方面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远不如封闭结构。因此,联盟号定型为“轨-返-推”构型,同时将逃逸方案设计为逃逸火箭带轨-返组合体一起飞行、之后以俗称“下蛋”的方式将返回舱单独分离扔下来。这样做虽然增加了逃逸的重量和机构以及动作复杂性,但保证了每次返回时处于高温迎风面大底的安全可靠。权衡利弊后取舍,代价是值得付出和可以接受的。

载人航天器还要为航天员和大型设备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因此,空间站上的密封舱通常采用大尺寸圆柱形作为主体构型,好为航天员提供尽可能大的有效活动空间,也可容纳大型试验设备。国际空间站甚至打破常规,以突出于舱段外表面、近似阁楼的形式设计了Cupola穹顶舱。今天,这个“阁楼”是航天员喜欢待的观察地球的“全景窗”。又因其突出于主结构之外,对空间站自身的观察条件也远优于普通舷窗,Cupola舱在来访飞行器对接空间站时也被用作站上飞行工程师观察和辅助机械臂操作的工位。


2000年至2007年,航天飞机完成了9次专门运输桁架组件的飞行——大多数单次上天的桁架组件重量在14至16吨。另有两次飞行,分别运输加拿大臂-2及其导轨。有了机械臂的辅助,空间站构型扩展的约束小了很多,而且能够在运输之后“改变”构型。前文提到的Cupola穹顶舱,就是与宁静号节点舱-3串列布置在航天飞机货舱中发射上天,再用机械臂单独安装在宁静号侧面,形成了“凸出”的构型。

中国空间站以三舱段组合形成基本构型。从各舱段到组合体,它们的“模样”都是系统功能驱动的结果:每个舱段构型设计必须满足发射和独立在轨飞行的要求,组合体则要作为完整系统形成有利于在轨长期工作的构型,并要有可行的组装手段。先看看每个舱段的构型。
天宫一号和货运飞船都采用了大尺寸密封舱加小直径资源舱的构型,资源舱外侧安装帆板和天线等需占据包络空间的舱外设备。然而,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并没有沿用这一思路,因为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和约束条件——前后都得接纳飞船和其他来访飞行器对接。前端是节点舱,后端也要有对接口和人员通道,因此只能将资源舱设计为直径达到包络上限的环形,“套”在密封通道之外。而对于密封舱部分,设计师将其分为大小直径两个柱段,帆板、中继天线、机械臂等大尺寸舱外设备都布置在小柱段,从而使其加上了各种“外挂”后的外包络仍在火箭整流罩允许范围内。小柱段内部则不能布置大尺寸设备,用于航天员生活休息。
就这样,核心舱演化出了大小尺寸密封舱加大直径资源舱的模样,同时各部分沿轴向形成节点舱-小柱段-大柱段-资源舱的顺序。基于这样的排列顺序及设备布局,发射时重量较轻的小柱段在上,有利于整体基频和强度设计,减少结构重量;入轨后,航天员生活区能够与工作区分开,相对安静、私密并且离节点舱近,应急情况便于撤离。
——实验舱。
实验舱没有前后对接的需求,只在一端对接即可。因此,实验舱的资源舱采用了传统的小尺寸“实心”布局,外部布置帆板、天线。
此外,兼顾到组合体构型,两个实验舱不仅尺寸、质量特性大体一致,从而获得整体构型下较好的动力学特性,而且从布局上都采用了工作舱-气闸舱-资源舱的顺序。对接之后,气闸舱成为所有密封舱组合的“端部”,意外时可以隔离而不影响其他舱段。

▲2021年4月29日11时23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成功。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各舱段的构型有理有据,舱段组合同样不是随意的。
由于我国空间站采用运载火箭发射各舱段入轨、上天后交会对接的建设方式,整体构型仍然得在“以节点舱为球心的辐射状”构型上做文章。但我们没有走和平号的老路,而是设计了中国特色的T字型。
三舱布于同一平面,形成T字;两个尺寸、质量特性大体一致的实验舱对向布置,形成T字的一横;利用每个实验舱自身近20米长的结构,结合各自资源舱末端配置的双自由度太阳翼驱动机构,两对大型太阳翼成为T字一横远端的两个“大风车”,不管空间站以何种姿势飞行,都能照上太阳从而获得高效的发电效果;两个实验舱的气闸舱分别位于T字一横的端头,正常工作泄压或异常隔离时均不影响其他密封舱段构成连贯空间,保证了安全性。
作为T字那一竖的核心舱,在这个对称关系中仍然保持着前、后、下三向对接的能力。后向对接货运飞船,使得组合体可以直接利用货运飞船的发动机进行轨道机动;前向、径向两个对接口不仅可以接纳两艘载人飞船实现轮换,而且保持正常三轴稳定对地姿态时两对接口都在轨道平面内,即可让载人飞船在轨道面内沿飞行方向和沿轨道半径方向直接对接,无需对接后再转换对接口。
对于航天任务流程而言,简洁不仅美,更是安全。

“设计不仅仅是外观和感觉,设计就是其工作原理。”(“Design is not just what it looks like and feels like. Design is how it works.”)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这句话,我非常赞成。
像所有航天器、以及在地球上工作的设备和系统一样,中国空间站的构型是设计出来的。设计,意味着它承载了特定的功能和使命,意味着它是在特定的众多约束条件下取得的优化解,意味着它凝聚了航天设计师在现有条件下创造最大价值的智慧。
当然,空间站的构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空间、时间两个维度上动态发展:实验舱I对接上核心舱之初,两舱空间站将呈大一字构型;实验舱I转位而实验舱II尚未对接时,两舱空间站为L构型;实验舱II刚对接上未转位时,三舱空间站是横向且不对称的T字形……除去这些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临时构型,中国空间站未来还可能在机械臂的辅助下进行扩展舱段的组装,进而形成十字形、干字形等扩展构型。
看上去,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不断改换构型。然而,变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来自设计,万变而不离其宗。
人类空间站发展已历四代。什么才是更好、更强大的空间站?简单比较没有意义,也没有标准答案。基于当代的科学技术,满足自身需求、契合自身能力,够用、好用、安全、高效的空间站,就是我们中国人自主设计、正在建设的空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