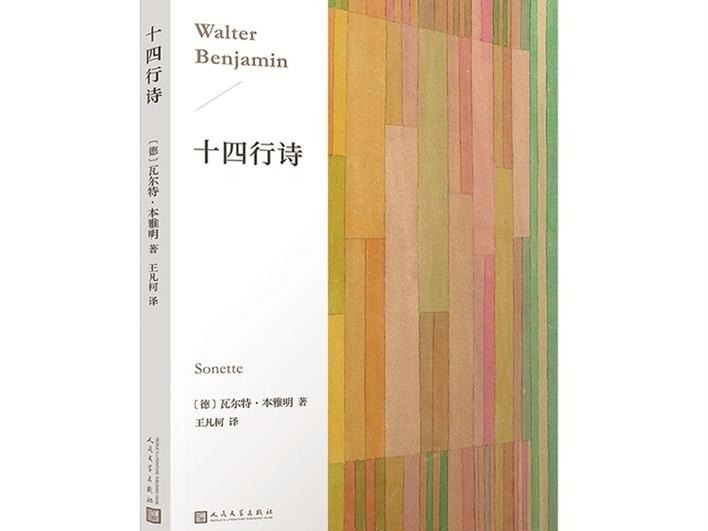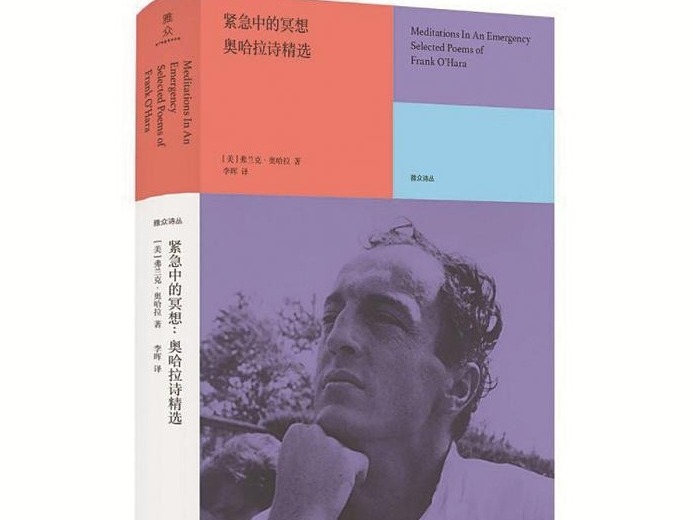《我们季候的诗歌:史蒂文斯诗文集》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 著 陈东飚 张枣 译 陈东东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一直以来,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国内都有许多读者,包括许多当代诗人,都非常热爱这位美国诗人。对他诗歌的翻译一直没有停止,曾有人统计过,他的诗歌《坛子轶事》,已经存在12个译本,未来恐怕还会有更多的译本出现。这本《我们季候的诗歌》,在我看来是一个史蒂文斯诗作的理想译本。
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我们时代两位重要的汉语诗人和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携手合作的——诗人张枣已经离世十二年,他生前的译诗不多,据说史蒂文斯就占了他译诗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是他比较用心也用力去翻译的一位诗人,而且是在他生前唯一出版的译诗集。诗人陈东东与张枣之间维系数十年的友情,他与陈东飚的默契,所有这些都赋予了这本书一种特别的意义,一个温暖的记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陈东飚就涉及史蒂文斯的翻译,从《最高虚构笔记》到《坛子轶事》《史蒂文斯诗全集》以及这两年又对《我们季候的诗歌》的重新修订,可以说陈东飚与史蒂文斯打了几十年交道,他非常了解史蒂文斯。在翻译方面,张枣与陈东飚两人的译诗观念不太一样,这本书中能感受到张枣的个人美学观念和陈东飚一贯的翻译理念碰撞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史蒂文斯。
本书的书名,用的是史蒂文斯一首诗的题目——《我们季候的诗歌》,有意思的是,它也是一度在英美学界引起争论的一个话题。据说,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美学界就“Whose Era”发起论争,休·肯纳(Hugh Kenner)认为20世纪英美文学属于“庞德时代”,布鲁姆就反对说应是“史蒂文斯时代”,理由正是史蒂文斯所写既符合“我们气候的需要”又恰切地再现了“我们的气候”。(引自李海英《伟大的尘世之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研究》)布鲁姆的这个说法恰好与我想谈的一个关于想象力的话题有点关系。我想结合一下诗歌《坛子轶事》(陈东飚译)来稍微谈一下这首诗。
我把一个坛子置于田纳西,
它是圆的,在一座山上。
它使得零乱的荒野
环绕那山。
荒野向它涌起,
又摊伏于四围,不再荒野。
坛子在地面上是圆的
高大,如空气中一个门户。
它统治每一处。
坛子灰而赤裸。
它不曾释放飞鸟或树丛,
不像田纳西别的事物。
史蒂文斯在《徐缓篇》里多次提到想象力。他提到两个命题:“1、上帝即想象。2、被想象之物即想象者”,然后推导出想象者是上帝。他也说过,“人即想象力,想象力即人”——其实,他还想说,人即上帝。人即上帝即想象力。反之亦然。在史蒂文斯的诗绪中,他把想象力的地位放到最高处,就像被放置在田纳西山上的那只坛子。《坛子轶事》首先是关于想象力、关于虚构的诗,也可以说,就是关于诗的诗。布鲁姆说史蒂文斯的写作恰切地再现了“我们的气候”,这个气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气候?在一个诗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他所身处的时代,他所身处的气候?他要如何把握这个气候,特别是一个人的写作跨度是半个世纪,如何在写作的最初就写下几十年后依然有效的诗篇?答案无疑是想象力。正像上帝是一种想象物的同时它也是想象者本身。以坛子作为象征的诗歌,它统领着一个诗人的身心,它被放置在最高的位置上然而并无实际的用途,它不曾释放飞鸟或树丛——《徐缓篇》里,史蒂文斯做出更具体的说明“一首诗未必释放一种意义,正如世上大多数事物并不释放意义”——但借由想象,它“再现了我们的气候”“使得凌乱的荒野环绕那山”——作为诗人,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也能再现我们所身处的气候,它取决于我们的想象,也经由我们的想象实现它自身。
(原题《放置在最高处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