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著《于坚论》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谢有顺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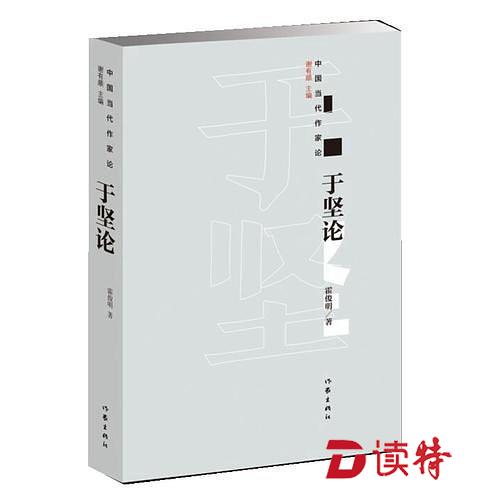
丛书所选对象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重点放在作品上面,覆盖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代表性、标志性作品上,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阶段性的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
于坚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这本关于于坚的专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论”“文本细读”和“文学批评”甚至“文化研究”,而更像是随笔、对话(潜对话)、印象记、读后感、杂谈、传记、索隐和评注。作者用诗人批评家的方式细读和还原于坚,在随意、散漫的氛围中寻找于坚诗歌、散文内部的秘密和多样性。
于坚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是场景、事务、物象、细节,“回到常识走向事务本身”。这些客观之物经过诗人主观情志的压缩和搅拌后形成了在场式的写作风格。即使于坚所处理的历史化的题材也是建立于个体感受和日常情境之中,尤其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使得个人与现实和历史形成了交互性结构——历史的个人化和个人化的历史。
本书对诗人作家于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中肯的评价,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认识,是了解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一个窗口。
内容节选
于坚早期代表作《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完成于1990年2月)与布罗茨基写作《黑马》和史蒂文斯完成《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一样,都通过“元诗”的方式在一个物象之上投注了诗人个体主体性的极为开阔、精深的观照。不同之处在于,《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几乎穷尽了一个诗人对“乌鸦”的所有常识、隐喻、语言、印象以及想象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于坚和布罗茨基在《黑马》一诗中做的是同一件事。《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也代表了此时于坚诗歌观念的调整与更新。这既与个人写作的转捩有关,也与当时整体性的时代精神境遇勾连。而早期的于坚,也不可避免和同时代诗人一样使用传统型的抒情性的隐喻和象征,比如1986年的那首《在漫长的旅途中》,那黑夜旅途中的灯光是“含情脉脉的眼睛”“黄的小星”,而灯光显然也是某种理想化的慰藉与精神呼应。而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则显示了一个诗人综合处理事物的卓异能力。多年后于坚解读了自己的这首前期代表作,“这是一场语言游戏,我与乌鸦这个词的游戏,它要扮演名词乌鸦,我则令它在动词中黔驴技穷。但是,这仅仅是语言学的游戏么,恐怕不是,这种游戏是富于魅力的,仿佛是为一只死于名词的乌鸦招魂。它复活了吗?我不确定。”
“词语的招魂”就是重新命名事物以及对词语的再度激活。这既与诗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有关,与语言的求真能力有关,更与当时汉语诗歌场域中一个诗人精神主体性的庞大和智性的反思能力有关。汉语诗歌只有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开始了反思和检视期,尽管这一时期仍然伴随着大量的毫无意义的诗人之间的争吵和不团结的火气与怒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在那一时期具有一定的写作和精神的双重启示性的意义。诗人如何完成对事物和精神性现实的命名,如何在有效的语言方式中虚构出更深层的真实,如何在一个物象那里穷尽所有的想象力,这首诗都做出了示范。
“乌鸦”是词语叙述中的“乌鸦”,显然已经不同于纯身体构造的鸟类(“在往昔是一种鸟肉 一堆毛和肠子”),也与饥饿年代诗人所企图征服的鸟巢里的肉体的具体的鸟有别,而成为精神对位过程中与日常表层现实和惯性的语言构造所区别的精神征候和象征物,比如对“黑夜修女熬制的硫酸”“裹着绑腿的牧师”“是厄运当头的自我安慰”“对一片不祥阴影的逃脱”的语法的反讽。这样的带有“第一次”言说和命名的难度是巨大的,需要对常识和语言的惯性进行双重的去蔽。
这是一只“语言的乌鸦”,是经由词语说出的另一种事实,“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焦虑,这种焦虑显然不是于坚个人的,而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在畸形的政治文化中,很多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定型和僵化,诗人的语言能力降到了冰点。为此,语言的焦虑一定会在特殊的情势下转换成为新的语言事实——对事物的重新命名能力的恢复。由此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将于坚的这首诗看作是一场八九十年代诗歌语言革命的一个并不轻松的诗歌语言学样本和案例。而这样一场语言的革命,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这种活计是看不见的比童年/用最大胆的手 伸进长满尖喙的黑穴 更难”。这实际上关乎以往整体性的象征、隐喻和神话原型系统。长满语言老茧的手要重新艰苦劳动,让那些老皮脱落,让那些新鲜的肉在阵痛中重新生长。于坚不是在与一只“乌鸦”作战,而是要与已经僵化的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作战。词与物的大战已经拉开——
我想 对付这只乌鸦 词素 一开始就得黑透
皮 骨头和肉 血的走向以及
披露在天空的飞行 都要黑透
乌鸦 就是从黑透的开始 飞向黑透的结局
黑透 就是从诞生就进入永远的孤独和偏见
乌鸦,成为诗歌代表的道德之恶与善之间的分界点。这种诗歌认识论的偏见显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吸附一切的黑箱,“乌鸦”正是那一只神秘难解的“黑箱”。诗人能否最终找到打开箱子的钥匙则未为可知,而打开黑暗的密钥只能靠那些真正具有创设性的诗人。就像乌鸦这只不祥的鸟一样,语言也是不祥的,因为任何挑战性的独立的语言都要经受住箭矢的“无所不在的迫害和追捕”,因为这同样是一个充满了“恶意的世界”。据此,诗人就是那个对笼统天空的打洞者,他手里拿着语言的钻头。某一个人人共知的公共性事物进入诗歌的时候其携带的集体印象以及惯见显然会形成吸附性,“你们 于坚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是一只乌鸦巢中的食物”。以往宗教的圣词、民间的巫词以及黑夜豢养的变形的“天鹅”并没有揭示出真相,而是一层层加重了认识的黑暗。“我丧失了对这个比喻的全部信心”,是的,诗人在命名过程中还要忍受准确的词语到来之前的失声和沉默,“我说不出它们 我的舌头被这些铆钉卡住”。当你说出一个词语,立刻就会有相反的情势出现。那些可见之物的不可见的暗示才是诗歌的内在秘密。“乌鸦”以及相似的事物使得诗人成为旋转木马,看似在飞速地前进但是始终围绕着一个固定的轴和中心而无法摆脱。诗人在语言漩涡中就是要挣脱这个离心力,当然要有接受挫败的心理准备,“我就想 说点什么/以向世界表白 我并不害怕/那些看不见的声音”。
此后,《在丹麦遇见天鹅》(1996)、《赞美海鸥》(1997)、《鱼》(1997)等这些“元诗”都是对传统诗歌物象学和语言学的反拨,从而掀起“白色的生物学的风暴”。
编辑 赵偲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