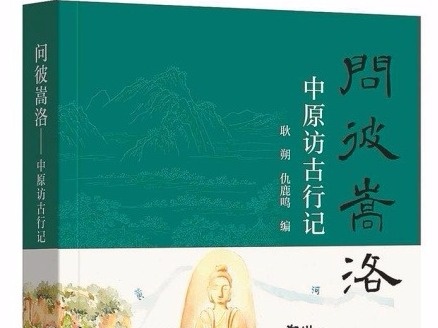第一眼见到紫蓬山的时候,确实有些吃惊——我老家皖东那地方的山虽然都不太高,但海拔起码都有四五百米,看上去都有山的样子;紫蓬山呢,远远看去,不过一浑圆的土丘(打听了一下,它主峰的海拔也就180米)。
这么轻率地以貌取“山”,显然有些浅薄。
紫蓬山有星罗棋布的庙宇,有大将李典的衣冠冢,有几百种鸟、几万只鸥鹭起落其间,有巢湖浩渺的烟波在远处闪光,还有许多跟文臣武将有关的传说,连它的名字也别有意韵——紫蓬,紫蓬,紫气东来,犹如蓬莱。
说“山不在高”,还是有道理的。一座山与那么多人,那么多建筑,那么多鸟有关,它脚下的烟尘被岁月染黄,它上空的云层被金戈铁马声刺穿过,如今,袅袅的梵音中,一只只精灵在此盘亘、守望,一座山有这么丰富的阅历,我老家的那些山自然望尘莫及。
时值深秋,我并没看到鸥鹭,它们已行脚远方;没去瞻仰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就静静地立在不远处,屋顶上有清脆的铃声在风中低吟;也没去瞻仰李典墓,世间本就嘈杂,何必再去惊扰一颗长眠的灵魂?我和同伴们在一片树林中喝茶,盘着腿,坐在蒲团上。茶艺师在演绎茶道,身姿曼妙、轻盈;音乐飘飘渺渺,像是长着翅膀,在林中翻飞。一只只白玉般的茶盏,一一奉至客人手中。这盈盈一握的茶盏托在手上,淡黄色的茶汤闪着琥珀似的光,轻轻抿一口,有香气和甘甜在唇齿间游走、流连。茶真是奇妙的东西,啜一口,心安静了一分,再啜一口,又安静了一分。
前方建筑的顶上,满是落叶,黄黄的,从空中往地上落,地上的叶子打着旋,往空中飞。其实,叶子那会飞呢,是风在飞。风,让凝滞的尘世有了声色和灵动,也让人神思飘忽;茶香浮动,人世如此可亲而真实。
茶是现煮的,是普洱还是铁观音,没留意,我被那些萧然、俊朗的树木牵走了心思。我又忍不住打量那些麻栎树。它们立在坡下,风纪严整,神情肃穆,像是正在接受检阅的将士。近的,肌肤触手可及;远的,俊朗的身姿隐约可辨;更远的,影影绰绰,似乎在向远方展示着自己的背影。曾经纷披的叶子,有的已经落下,有的正在逃离,树干得以更彻底地展示它们的筋骨。在我的印象中,越是挺拔高大、堂堂正正的树,旁枝越是稀少,麻栎树也是这样,朴素、简洁、敞亮,家底一览无余,像是一位坦坦荡荡的君子。 我很喜欢叶子落光了的树。小树也罢,老树也罢,每棵树都精气神十足,俨然准备与来势汹汹的严寒赤身相博。这样的肉搏总是悲壮的。一些树没斗过严寒,死在冬天里,而更多的树则是带着伤痛,活到了春天,然后吐故纳新,自我疗伤,再迎接电闪雷鸣,迎接下一个严寒。
树总是让我敬畏,它们大多活得比我久,比我见过更多的风霜雷电、细雨和风,经历过更多的欢畅和苦难。面对一棵树,我常常自惭形秽,默默地低下头,而面对一棵枝干浓黑如墨的树,我有时会有流泪的冲动——它要熬过多少风霜雨雪、酷暑严冬,才会蜕变出这一身的老气?不是老气横秋的“老气”,而是一派不言自威的庄严。庄严,是一棵树,也是一个人最神圣的尊严。
我这么看着树、想着树的时候,茶的香气在漂浮,音乐被风吹得支离破碎,天光也被吹薄不少,林间有些昏暗,头上的天灰蒙蒙的,似乎一场大雪即将倾泻而下。我忽然有些激动——要是真的有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我独自置身于紫蓬山的麻栎树中,会是怎样的一场体验?
风可能从东边来,可能从西边来,可能从南边也可能从北边来;雪也许从天空往地上飘,也许从地上往天上飞,它们起初下得不紧不慢,但渐渐地密了,又下得紧了;风打着口哨,从旷野里杀过来,雪借风势,漫天飞舞,天和地就这样神奇地连成一片。那无边的雪落在庙宇的屋顶上,落在树梢上,落在泥土上,落在我的头发上,落在我的脸上,落在我的身上;我的心中,也是狂风呼啸、大雪纷飞。这一刻,天是白的,地是白的,树是白的,世界是白的,我也白成了天地之间的一棵树。
我和那些麻栎树一样站立着,雪抽打着我,抽打着那些麻栎树。我看着那些麻栎树,它们也看着我,我们默默无言。这一刻,世界如此简单,天地如此亲密,我和那些树如此洁白。 这一刻,我如此安静,如此干净,如此幸福。
编辑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