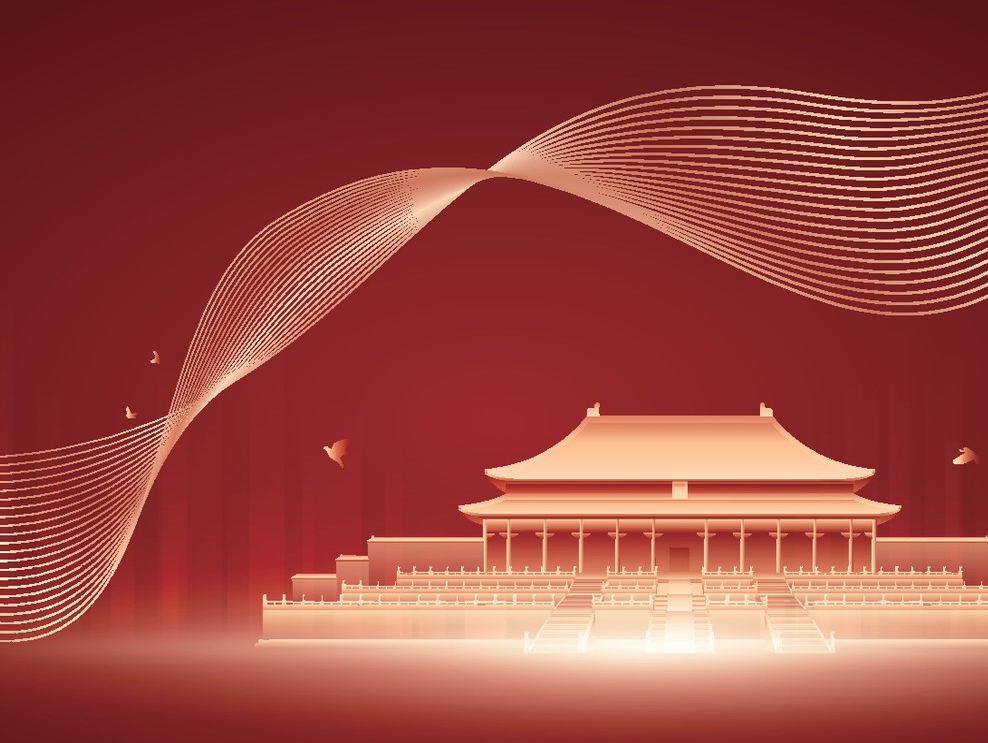大师就是道路
大师不是匠人,不是一般意义的先锋,不是将某种风格或传统发扬光大者,他们不会沿袭某些固有的程式,更不会刻意向某些人致敬。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大师就是先知,他们开辟道路,甚至,他们就是道路——后来的人通过这些道路抵达新的目标,并发现更多的目标和道路。

这是我在获悉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逝世时,反复想到的话。
因为无法概括阿巴斯意义,我就再次翻阅他的诗集《随风而行》,并重新浏览他的多部电影经典——如《樱桃的滋味》、《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随风而去》、《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以及他最后完成的剧情长片《如沐爱河》等等。我蓦然发现:他电影里的人,几乎都是在或寻找或行走于路上。在诗集《随风而行》中,收入了阿巴斯的221首极为简约的短诗,却鲜少出现道路的意象,而在诗外的指向里,却无不通向或现实或想象的路。比如这首:月光皎洁的夜啊/一百兵士从命/早早回了营房//做叛乱的梦。全诗只有四句,加中间一个空行,没有一处提到道路,现实与梦境交织,诗意与谋反共存,充满未名的路径与动态的行走。最重要的是,他在士兵的梦中注入了“叛乱”,这是所有先知或艺术大师或革命者,面对现实时基本的精神气质。就在这本诗集里,有几十幅阿巴斯自己拍摄的照片,几乎所有的风景里都有道路点缀其间,它们多是荒寂的,原始的,崎岖,坎坷,或被泥石或被冰雪所覆盖。想到阿巴斯之于世界电影,之于艺术,之于创造的意义,这些黑白照片让我有种醍醐灌顶般的顿悟,我想说:阿巴斯就是道路——他以自己的电影和毕生的努力为后人后世开辟着新的方向。

2008年的8月29日,我在第6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看了惊世骇俗的电影《希林公主》。关于这部电影,此前其实一无所知,只知道其英文名为《Shirin》,是阿巴斯导演的最新作品,选择该片作全球首映,是因为要为阿巴斯颁发电影节专设的第二届“导演万岁奖”。我第一次见到了阿巴斯本人,他和日本导演北野武一同在剧场中间亮相,面貌丑陋的北野武好像成了他的陪衬人。阿巴斯照例戴着招牌大墨镜,高大,儒雅,魁梧,英俊,犹如大神君临,台下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阿巴斯从北野武手中接过奖牌,微笑着并不言语。说相声出身的北野武似乎有些慌乱,他张口结舌地用日语致词,大意是说:阿巴斯导演在日本非常受欢迎,我能够把奖颁给他感到十分光荣。随后又逗趣补充说,“希望这条新闻传回到日本国内时,我在日本的朋友们都能相信。”那天下午,简短的颁奖仪式后,开始放映阿巴斯的新作《希林公主》。说这部电影惊世骇俗,是因为它几乎摈弃了所有剧情片的元素——讲述的是12世纪波斯的传奇故事,却没有一个历史场景和人物,观众眼里看到的只有看电影里的观众。后来才知道,银幕上的这些观众并非真的普通观众,而是由不少演员扮演。剧场里的我们看到的电影《希林公主》其实并不存在,它是在银幕上的观众眼里,我们只是看观众之看。换句话说,电影不在现场观众的视野,我们看到的只是银幕上的观众——通过他们在观影时的鲜少变化的表情,以及随着传来的对白和细碎音响,来揣测银幕上发生的故事。说它怪诞,说它实验,说它匪夷所思,都难以概括观看时的具体感受。这是一次艺术的颠覆,一次电影的探险与革命——彻底抛弃了当下电影的叙述方式,古代与当下,传统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观看与被观看,所有的边界都被打破了。观众必须全神贯注,必须调动最丰富的联想,但也未必能理解其内容的万分之一。对于现场观众来说,这样的电影无疑是巨大挑战,也许会昏昏大睡,或者拂袖而去,或者克制着试图理解。无论如何,它绝对是一部前所未有,令人脑洞大开,激人想象,引人深思的电影。
那天下午,我从威尼斯剧场走出来,仿佛刚刚从黑暗的往昔回到现实。电影营造的氛围突然立体退去,置身在水城灿烂阳光下,我有种缓不过神来的感觉,刚刚置身的遥远古代、遥远东方,以及那些似曾相识的观众都到哪里去了?想到刚刚颁发的“导演万岁奖”,想到阿巴斯和他非同寻常的电影,比如获得诸多国际殊荣并引领了世界级的伊朗电影现象的名作《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随风而去》等等,虽然有些仍备受争议,但带给世界观众的感慨与感动以及对电影疆界的开拓,都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我忽然强烈意识到,当人们都在危言“大师已死”时,其实大师就在身边。像所有先知的命运一样,他们打破边界,披荆斩棘,发现和创造新的可能,开辟新的道路,只是不被当下的人所认可。

伟大的电影都是诗篇
大约在二十年间,我断断续续看过阿巴斯各个时期的电影代表作。就像看一些最先锋的作品,有些喜欢有些不大喜欢,有些看了痛彻心扉,有些却似懂非懂。即使是公认的名作,也往往会经过曲折的认识过程。我曾专门撰文阐述诗意是拯救电影的春药,文中举了很多例子,但没有以阿巴斯的作品为例,因为阿巴斯本来就是诗人,他的所有电影都是或抒情或写实的诗篇。在我看来,所有堪称伟大的作品都是诗篇,所有堪称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诗人。以此来衡量作品的高下,方法简单,屡试不爽。
在我早期的电影随笔集里,曾评介或赞美过《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影片,但在后来重温时,仍觉得似乎并没有理会其中更多的深意。也许这就是经典的特质——每次重看都会有新的意会和发现。
当《樱桃的滋味》获得1997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时,因无缘看到影片,我就先在《世界电影》杂志上将剧本读了一遍。坦率地说,剧本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感同身受——一个名叫巴蒂的中年男人驾车寻找一个能帮他自杀的人,在表现这个寻找过程时,影片几乎没有戏剧化的情节。甚至我着意搜寻的樱桃场面和寓意也告落空,后来看过这部有着纪录片气质的影片,竟也发现确实没有樱桃的任何意象,只是在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口中提到过,他不厌其烦地劝阻巴蒂先生打消自杀念头:“……你想否定一切吗?你想放弃一切吗?你想放弃品尝樱桃的滋味吗?别这样,我的朋友,我请求你别这样!要是你非要这样,我也没办法!”影片没有由樱桃展开,却有段关于桑葚的诉说。动物标本剥制师对巴蒂讲了自己企图自杀的经历——当他将绳子朝树上挂准备上吊时,手偶然碰到了软乎乎的桑葚,他吃了一个,意外品尝的美味让他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他本来是去自杀的,却带回了桑葚。电影中的主人公最后还是躺在土坑里,等待有人来埋葬他。但在最后的影像里,人们发现这是一部正在拍摄的电影。阿巴斯为何不将影片叫做“桑葚的滋味”而叫“樱桃的滋味”呢?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也许,没有出现樱桃的“樱桃的滋味”更能激发人们对樱桃以及喻指的生命意义的联想。后来,看到更多阿巴斯的电影,才知道,阿巴斯几乎所有作品都有这样出其不意的特质。就像他的影像语言,多以写实的面貌出现,土气,粗浊,不雕琢,不美化,不抒情,却超越了世俗,而回荡着天籁之音。这正应和了绝妙好诗的特点——朴素天成,无中生有,余韵悠长。
阿巴斯的诗意体现在他电影的所有生活琐碎,甚至不堪入目的情境里。需要观众的体味与发现,随便一个看似随意的镜头都绝非随意,而是大有深意,耐人咀嚼。比如,剧情长片《如沐爱河》,讲述的是日本援交少女与一个寂寞老鳏夫的交往。电影开始时大约有十多分钟的咖啡厅里的电话和交谈,人物对话全部是不动声色的错位,每个人的状态都稀松平常,细碎中却折射出人物特定的个性与职业特点,虽然只是过场戏,每个镜头却都曲折多变,复杂耐看,诗意盎然。
大师是说不尽的。对于阿巴斯电影的评介,最著名也是具有“一句顶一万句”般的惊人之语出自戈达尔——电影始于格里菲斯,终于阿巴斯。在我的理解里,这个“终”不仅仅是终止和结束,更是一个新的开始,如同在越来越同质化的大漠中迷失的人们,左冲右突,慌不择路,这样的时刻总能在荒野里寻找到某个前行的背影。
这个背影,或说所谓终结者或者说先知,就是阿巴斯。一如文学界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卡夫卡,穆齐尔,佩索阿,或美术界的伦勃朗、梵高,他们超越时代,我等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只能置身其阴影下,感受其庇荫却未必能懂得感恩。大师的高度不在当下的计量里,也许我们一时难以理解和意识,但随着时间的淘洗,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独到、精彩和伟大。
编辑 白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