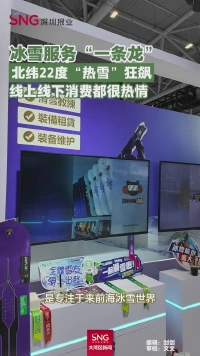目则珠江
看完艾吉倾注心血创作的长卷散文《梯田里的哈批》,被其炽热的赤子之情感染,接地气的土言土语从梯田边不时冒出来,直击人的心脑。
“我写作,不过是把一些感动我的人事、风景,用文字记录下来。”艾吉纯粹的记录,让读者留下想象领域和思考空间。
梯田和梯田孕育出的丰富文化,一直以强大的力量深深扎根在艾吉的故乡。不含杂质的写作,首先体现在其对梯田的一份敬畏之心上。
梯田是全书的核心,如何阐述这一思想,显得尤为重要。作者可谓下足了功夫,从梯田掠影、一丘大田、一生围着梯田转、梯田工具词典、田园的家、梯田野味、祈福的习惯、围拢在火塘边、集体仓库、终生牧人、牛亲家搭起民族情等主题看,作者采取俯瞰式掠影、细致刻画、延伸解读、深入挖掘等叙述形式,在文中呈现了哈批梯田独具特色的形与神。
梯田是哈尼人当初为了生计一锄锄挖出来的,如今梯田享誉世界,可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哈尼人与梯田最好的双向奔赴。在这样的互相成就中,作者于哈批的全景式记录,无疑具有管中窥豹的效应,是对哈尼人奋斗不息精神的深情记录,也是一份献给故乡梯田的敬畏之作。
哈尼人的命运与梯田联系紧密,他们在与梯田的朝夕相处中,一点一滴去了解梯田的脾性,也在相看两不厌的互相欣赏中,发现了彼此的价值。如,“那些一代代在山上一锄锄雕刻梯田的人们,为了填饱肚子,在几乎对生存失去信心的绝境中,从大自然身上学到了生生不息的精美技艺。他们来到世上,命就像秧苗插进梯田,他们的人生,绕来绕去通向梯田。”
作者从不吝啬对梯田的赞美,时时不忘感恩梯田的滋养与馈赠:“如同红河州的每一个哈尼村庄,是梯田,养育了哈批。当冬季挖好梯田,它们是一片片明净的天空,每丘田里,像鸭子,凫游无数颗金色的太阳。”
艾吉的创作中,最大的特点是能把宏大主体表达藏匿于细微的人物形象中,在其独特叙述中,向读者呈现一份对生活的个性化理解。
写哈批的历史,作者更多体现在人物身上,以普通人的个性凸显村子的主体气质。哈尼族的娃娃,到一定时候,母亲就要背在身上,到田边进行象征性的劳动教育。在勤劳上进的哈尼精神浸润下,艾吉的文字也如其人一样,在绵柔中藏有锋芒,在温和中充满力量。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作者始终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同胞的温情,这点集中体现在卷二的泥土人生篇里。
作者笔下的哈尼同胞,形象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如烤酒、白衣裳、阿巴尼、笑话高手、第一个高中生等,既有鲁迅笔下的“润土”,也有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个个立体形象,充满了泥土气息。
对同胞性格情感的深刻细致描写,源于作者常年与同胞老乡间深入交流的积累,源于其内心深处对同胞的一份温暖情感,正如其自白所言:“为故乡写本不含杂质的书,是为告慰死去的先辈,也为温暖尘世的生者。”
“人有故乡是幸福的。人能够爱故乡是幸福的。别人问我,你最爱的地方在哪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故乡。”
作家笔下,故乡是一个高频词,如路遥书中的黄土高原、莫言写作中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文字构建的额尔古纳河等。艾吉也一样,他对故乡哈批的依恋和感恩之情大胆而直白,毫不掩饰。
“不论你飘落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故乡——这个伟大的字眼永远是唯一的,走千里行万里,它都会使你风尘仆仆地回归,释放心中的怀念之情。”作者借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玛特托夫的名言对故乡深情告白:自己到死,都是不折不扣的故乡的一株庄稼。
作者对故乡的表达,始终表现得客观,情感也在浓郁表达中有所克制,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生活体验所感所悟,让人读出了真诚、品出了感恩。
全书的叙述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作家以介入者的角色雕刻故乡的群像,显得冷静而客观,既没有借故乡炫耀自己的意思,也没有刻意拔高故乡形象的表达,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叙述,让人有如沐春风的阅读体验。
在读《梯田里的哈批》过程中,常常会浮想联翩,联想最多的作家是沈从文。常常会在艾吉笔下的哈批村里发现沈老笔下同样质朴唯美的茶峒村的影子,都对故乡充满虔诚、充满敬畏。作家对故乡的情感酝酿,既需要时光的沉淀,也需要一定距离的感触。对于从小在故乡哈批生活12年的艾吉,经过到红河县、个旧市、蒙自市打拼多年后,再以“客人”的角色回望故土乡情,其整体的叙述既有浓郁的情感,又表现出一份客观的表达、理性的克制。
正如沈从文以《边城》为心中美好爱情正名一样,艾吉的《梯田里的哈批》也有为故乡奉献一次不含杂质的写作,为世人展示质朴哈批的美好意蕴。
阅读、写作,其当下的最大意义无疑是在变动不居中找到一份确定性。《梯田里的哈批》,其人、其文,无疑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扎根泥土、扎根生活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