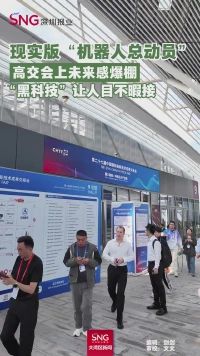艾建桥
在我们当地,爷是对父亲这一辈分的尊称。三爷的大儿子阿杰,一个月前来深圳,在一家建筑工地上做泥工。一天晚上,我与阿杰通视频电话。我们多年不见,他的眉骨、下颌线像极了三爷年轻时的模样。往事如烟,有一种爱,一直种在我的心海。
三爷姓王,按辈分该叫叔,但父亲总说:“你三爷自小在你奶奶膝下长大,论感情比我们亲兄弟还亲。”于是我们兄妹都跟着喊“三爷”。
三爷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嗓门如洪钟,对我非常关爱。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菜,一定会叫我去品尝。在上世纪80年代,夏天能吃到西瓜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卖西瓜的人走街串巷吆喝叫卖,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掏钱买,大多数人家都是拿家里的废品交换。三爷拿家里的废品换了西瓜后,偷偷叫我去他家里吃西瓜,还特意叮嘱我不要对外人讲,可见三爷对我不是一般的宠。
三爷曾救过我两次命,这件与个人生命攸关的大事,让我终生难忘。七岁那年,一天阴沉沉的,正是农忙时节,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我在三爷家门口玩耍。门口有一个池塘,是村里灌溉农田的“当家塘”,前两天下过几场雨,池塘的水满且深。调皮的我将当时浸泡在池塘边的“秧把”(那种扎成小捆的秧苗)抓在手里抛来抛去,觉得溅起的水花挺好玩,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抛向水面,抛着抛着,或许是用力过猛,脚下站立不稳,一个趔趄,整个人倒向水中。我只觉得眼前昏暗,池塘大量的水向我的身体汹涌而来,将我吞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双有力的大手将我的身体从水中托起,原来三爷刚好在大门边搓草绳,他突然听到水里“扑通”一声响,并且陡然不见我的身影,就知道大事不妙,当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水里,猛然抓住我的身体,把我救了上来。
还有一次,我突发疾病,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上昏死过去。等我在医院醒来,父亲红着眼眶说:“是你三爷背着你一路狂奔,在公路上磕头求助,才拦下一辆货车送你来医院抢救。”我望向病房门口,三爷正靠着墙打盹,右腿膝盖有道新结的血痂——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拦车磕头时公路上的碎石子磨破的。医生告诉父亲,幸亏送医院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上初中时,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经常和父母顶嘴。三爷就给我上“道德课”,他卷着旱烟,用粗粝的大拇指敲我脑壳:"你爸妈弯腰割稻子时,腰杆压得比田埂还低,你倒学会使性子?……”在三爷苦口婆心的开导下,我低下头,当着父母的面承认错误,也是在三爷的劝诫下,中考失利的我,顶着压力复读初三,最终考上了当地的技校,顺利完成学业。
2003年我南下深圳,三爷硬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有咸鸡蛋和干鱼仔。同年他癌症晚期,电话里三爷喘息粗重,仍叮嘱我在外要照顾好自己。而我,在他病重的这段时间,居然未能回乡探望。当三爷病逝的噩耗传来,我正奔波在送货的路上。
三爷为我续了两次命,侄子不孝,他生前对我如此关爱,我竟然没回家看他。当天夜深人静,我走出宿舍,在楼下的僻静之处,对着北方的故乡,叩了三个响头,算作我对三爷深深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