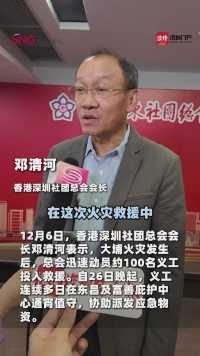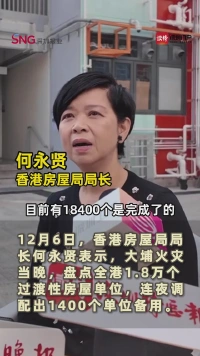李凤琳
临近端午节,本地朋友特地给我送来手工制作的广式咸蛋黄肉粽,我的味蕾再一次被征服。早餐时分品味咸香可口的粽子时,我思绪纷飞,倏然跌落至童年的回忆中……
几场梅雨过去,江南正式入夏,枇杷黄了,杨梅红了,洞庭湖上空的烟雨渐渐消散,空气里弥漫着清浅荷香与艾蒿香。
童年时光是清贫却快乐的,每个传统节日都在我们的望眼欲穿的期待中隆重登场。端午节的重头戏就是吃粽子,喝麻花肉汤。
过几天就是端阳,把柜顶上的糯米拿下来吧,母亲轻声吩咐蹲在门口抽烟的父亲。在一旁闻言,我们姐弟分外开心,心里明白,很快就有白米粽子吃了。
五月初五的清晨,母亲顶着一头露水回来,手里多了一把青翠欲滴的艾蒿,里面夹带有叶片扁长的菖蒲,我知道,这是她从堤坡下不远处的沟渠边采来的。她麻利地把艾蒿与菖蒲分为几份,分别插上大门门框一角和各个房间的窗户上。彼时我不太懂得这种习俗的缘起和意义,但是特别喜欢节日仪式感,也非常喜欢艾蒿独有的清香气味。平时也会遵照母亲的嘱咐,采来艾蒿煮水泡脚洗澡,母亲说可以去火、解凉和驱蚊。
事先淘洗过的糯米经过几个小时浸泡,喝饱了水分,一颗颗莹白饱满,宛如白胖圆润的珍珠。母亲摘来新鲜的箬竹叶,在河边清洗过,盛在竹篮里拿回家。待锅里的水沸腾,箬竹叶纷纷跳进锅里,随即又被捞起来,放置在大木桶里,加满清水,上面用一块石头镇住,防止有调皮的箬叶探出头来。这样的箬叶能保持湿润柔软,还能蓄满自身的草木清香。
堂屋里摆好了木桌竹凳,陶瓷盆里装好了大半盆糯米,控好了水分的箬竹叶整齐地躺在簸箕里,矮凳子上有剪刀和细长坚韧的蒲草。
白米粽子没有用任何馅料,食材只是纯粹的糯米,特别简单,却蓄含我童年时代最淳朴最厚实的期待!母亲双手灵巧,上下左右翻飞如蝶。三片竹箬叶交叉一叠形成一浅坑,加入一勺糯米,两头封口,再用蒲草前后一扎,绕到中间部位拦腰缠绕几圈,一勒紧就顺势打个结,剪刀咔嚓一声,多余的蒲草应声落地,一个肥肚尖头的圆锥状白米粽裹着翠绿竹衣的粽子就成型了。慢慢地,旁边空着的簸箕里堆满了清一色翠衫小粽。
母亲先去灶屋生火烧水,接着将粽子放进空心圆柱体的竹甑里,置于锅中蒸煮,盖上木盖,桶沿与桶盖周围的缝隙再用湿毛巾塞紧。灶里火焰腾腾,很快,水沸腾起来,灶屋里雾气萦绕,灶屋外,笑语盈盈。母亲不停地往灶里添材,往锅里加水,糯米饭与竹箬叶的香味融合在一起,飘散出来,勾得我们四姐弟肚子里的馋虫蠢蠢欲动。终于,几个小时熬过去了,母亲满脸汗水从灶屋走了出来。我们一拥而上,殷勤地端茶倒水。母亲笑吟吟地对我们说,先去写半个小时作业吧,我去村口买点白糖割点肉。
这个时候写作业自然是敷衍,但我还是装模作样打开了书包,耳朵却跟随母亲的脚步声走了。从灶屋里飘出来的香味顽固地钻进我的鼻子,无法拒绝,也赶不走,便在心里默念着,妈妈快回来!
很快,母亲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感觉她进了灶屋。我再也按捺不住,馋猫一样顺着粽香味溜进了灶屋。母亲不急不慢,生火烧热另外一口锅,舀水做汤。随即,母亲切肉打鸡蛋,又变戏法一样拿出了一串金黄的麻花。弟弟妹妹们也闻声赶来,围着灶台看母亲做美食,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眼珠子都要掉进锅里了。
终于开饭了!母亲端着麻花肉汤上桌,用碟子盛了白糖摆在桌子中间,接着揭开锅盖取出十数个热气腾腾的粽子来,每个人碗里各两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蘸白糖吃粽子,喝麻花肉汤,说着家长里短,欢欢欢喜喜。
时光匆匆,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到了当年母亲那个年龄,如今生活丰盈充裕,每天都像在过节。又是一年端午,家人团聚,各式各样的粽子被摆上餐桌。我尤其喜食广东咸蛋黄肉粽,咸香软糯,口味醇厚,肥而不腻。不过,总是隐隐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它缺失的是我童年夏天的雾水、艾蒿、菖蒲、箬竹叶、麻花与白米粽以及当年简单朴素的幸福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