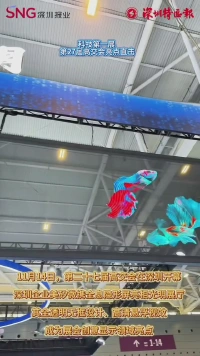再过两天就是父亲的祭日,屈指算来,他老人家已去世了三十一个年头了。本来想在他前些天的甲辰七夕诞辰之日写点念想,可因手头忙碌,就无奈放下了。近日晚间,仔细地阅读了大哥初撰的家乡村志,更加激起了对父母亲的思念。
在生活中,越亲近的人,即使过日子相处得越多越久,往往难以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照亲人的日常行为细节,这就像看油画作品一样,越近越模糊,越远越清晰、越动人。
而我童年时期的父亲形象,父亲的举手投足,父亲的做人做事,就像这记忆中的油画一样,时间越久远,反而看得越清晰,越栩栩如生。
父亲的鞋子
父亲爱干净,还是在年轻当话务员工作时就出了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鞋子的爱惜和“讲究”。
父亲早年因病回乡种地后,在伊川县江左乡白土窑村第三生产队当了牛把子,每天一大早就要赶牛出工,不是耕地,就是耙田,不是拉车,就是打场,一年四季,大多数时间里,要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松软的黄土地中行走,母亲做的布鞋即便是再结实,也经受不起这种劳动磨损。

20世纪80年代末的夏日,父亲病后坐在大门外的院子里。 供图:伊汀
你会看到,凡是在乡村里做牛把子的,除非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没有几人能经常穿着簇新的干净黑布鞋出现在邻里面前,都是把一双破损的旧布鞋穿到不能再穿为止,庄稼人把鞋子看得实在是太金贵了。
而我所知道的父亲却与众不同。
每当早上耕地出工回来,他先要把两头牛安顿好,喂上草料后才回家。父亲进大门前,在地上要先跺上两脚,把鞋帮鞋底还沾着的泥土跺掉,在前院坐下来后,又用鞭杆把鞋窠篓里已结块的泥土再掏干净,轻轻地朝地上磕上几下后,才把这双鞋子整整齐齐放置在西厢房窗户下的台阶上,然后再换上一双干净的黑布鞋,这才从容地去洗手擦脸吃饭。饭罢,当听到生产队长出工敲钟的声音后,他再换回上地干活的鞋,继续去赶牛上地耕作。
记忆中,父亲这道换鞋的程序,有条不紊,不厌其烦,伴随着他的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好多年后,我上了大学,这一情景才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在春夏秋三季的时光中,父亲似乎只有这两双尖口黑粗布鞋,一破一新,一双是耕地出工劳动所用,一双是要走亲访友、迎来送往,或上街赶集,这双鞋成了父亲的脸面。
对一个辛劳的庄稼人来说,在农村环境中,这种对鞋子的“讲究”实不多见,也许是父亲年轻时曾经见过“大世面”吧,尽管穷了一辈子,但要脸面,从一双鞋子上,我深深感受到了父亲的自尊与自爱。遗憾的是,父亲虽然爱美,喜欢鞋,可一辈子也没能穿上一双心仪的好鞋。
常言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已过了大半辈子,现在才由衷感悟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有多深,这是不言而身教的潜移默化,而不仅是遗传基因的驱动。
我喜欢穿有品质的鞋,看重鞋,也爱惜鞋,一年四季里,鞋子也是换着穿。现有的几双皮鞋,时间长的有十几年,短的也快六七年了,整体看上去,还和新的差不多。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爱干净,但对鞋子自觉清洁护理,就像父亲一样,这一习惯几十年没有变。
其实,除了我们这一代经济条件后来好起来的原因外,是父亲生前对鞋子的珍爱态度与好习惯,恰如春风化雨般浸润着自己的心灵:当人有了对生活的热爱,也就有了对美的珍爱。
我曾记得作家贾平凹写过的一句话:“女人的美在头上,男人的美在脚上。”这也是让我有共鸣感,并深深铭记的一条生活美学法则。
一个人每天负重前行,最累的就是踩着大地的双脚,即使有这般那样的委屈,也不能再委屈了它,试想,若能让天下每个劳动者的双脚都美起来、健康起来,那该多好呀!
父亲的耕作
说到父亲经常换鞋的往事,这都是和他做牛把子劳作有关。
父亲是一个当了几十年生产队的牛把子,闻名于周围的三里五村。风里来,雨里去,年岁日久,他与村西岭上下的田地相伴,与两头老黄牛朝夕相处,相依为命。
父亲个子不高,干重力气活在乡村没有优势,但他行动精干,有军人风范,每做起一件事来,有条不紊,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现在想想,父亲当牛把子可能是最适合他做的工作了,因为养牛要用心细心,耕田赶车需要技巧和耐心,对那些有憨力气但粗枝大叶的人来说就没有优势了。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从公社到大队,再到生产队,整个社会是集体经济和集体劳动,每个劳动力靠出工多少来挣工分,一个壮劳力,一天出三次工(早上2分、上午和下午各4分)挣10分,牛把子相当于当时的技术工种,也可以挣到10分,还能在生产队领取牛饲料。这是一种常年慢跑式马拉松的农田活,若要每天挣到这10分,除了自己的身体要吃得消,无病无灾外,关键是能否把牛喂得好,勤出工才行。
上小学时,我是看到过父亲耕过的田,耙过的地,直观的印象,就是直溜、平整、干净,又有条理,远远看去,玄黄之间,像家乡荆梢梁岭坡地上的一幅抽象画。
大哥在《失去的岁月》的自传性文章中写道,父亲“犁耙地的技术是村里所有的牛把子都望尘莫及的。特别是耙地中的迭耙活,不同的地形采取不同的耙法 ,还起下好听的名称,像什么‘老犍磨’‘架鸡尾’‘升子底’‘一杆旗’等等,他都样样精通,耙过后的耕地上,耙纹圆如盘,直如箭,地面平整,小坷垃也没有,不论是三尖葫芦头的地块,还是地中间有坟头石坎,绝不留死角,看着令人觉得种田简直像是加工艺术品。父亲耕地是在创作一幅完美的图画。”
曾身为民办教师亦教亦农的大哥,今天还遗憾自己没有把父亲耙地的这种手艺学到手,而作为长子的他,更是由衷地认为“父亲是耕地能手,一丝不苟、尽善尽美的榜样”。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为什么能把生产队里的农活做到这样的极致?其实是功夫在诗外。父亲养牛爱牛惜牛,深通“牛”性,那时正处壮年,上老下小,生活依托,全赖他所调教的这两头黄牛,其中一头小牛从接生到老,都是父亲没日没夜喂养照料的结果,要知道,这些牛可并不是自家的私有财物,而是集体的财产,但一生能做到真正的公心,这才是我敬佩父亲之所在。
每到深冬的夜晚,村子西寨壕的窑洞里暖融融的,当喝罢汤后(当时豫西农家因粮食少吃晚饭称“喝汤”)的村民们闲来无事,都会聚集在这温暖的窑洞里,听讲父亲打仗的往事,父亲一边和前来的晚辈人侃大山,一边会不停地铡草添料,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这些不会说话的牲口。不难想象,天长日久,父亲就是这样去通“牛性”的,若老牛有灵,又何尝不会通“人性”呢?
人们说,一个好的司机,能够驾轻就熟,贴地行驶,贵在人车合一,心手合一。而父亲能与朝夕相伴的两头老黄牛默契配合,是把在大地上的耕耘变成了艺术品一样的创作,这是爱土地、爱工作和“人牛合一”的必然结果吧。
父亲的穿衣
我对父亲早年穿衣着装的印象模糊,父亲和普天下在田地辛劳的绝大多数农民不会有多大的差别,夏穿粗布白衫,冬穿黑粗布棉袄,似乎年年如此。
听大姐讲,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有照片的。据说,那是他打中条山战役前,在洛阳城穿着军装照的。
可惜的是,日本鬼子后来占领了豫西,由于我们家乡地处中岳嵩山西南麓的伊川、登封两县交界一带,是豫西抗日打游击的主战场,日本兵来报复扫荡,无恶不作。奶奶担心这些照片和军衣被搜出来惹祸烧身,就下狠心,一张不留地给烧掉了,父亲年轻时的形象在我们后人的眼里就成了空白,我们兄弟姊妹家里现在留存的父亲的照片,也大都是晚年有限的几张了。
我对父亲穿着的关注,是在他20世纪80年代末脑中风康复期间的记忆。
过去在农村,人们还没有对家族遗传病的认识。爷爷在20世纪的60年代中,因高血压脑中风失语偏瘫,去世前的四年多里,一直不能自理,需要父母亲穿衣喂饭,床前伺候。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平常精力充沛、六七十岁还正常下地劳作的父亲,却因高血压病引发脑中风,在冬天的某个早晨,翻不了身,起不了床,说不出话了。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父亲不抽烟,不喝酒,日常吃的粗茶淡饭,无油水可言,十几年后,爷爷的命运,却如出一辙地复制在了父亲的身上。
幸运的是,由于在家对父亲及时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输液、针灸和中药齐头并进,母亲和全家人无微不至的护理,多管齐下,非常及时地控制了病情,父亲把中风后遗症限制到了最小的可能,祖父病后的厄运没有在父亲身上重演。
年纪大了,脑中风后遗症康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除了按时服药治疗,病人要有达观的心态,更要有积极锻炼的自理能力。父亲病后在世的七年多,是乐观与坚强的七年,在点滴小事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一生所坚守的自尊、自爱与自强,还有不给人添麻烦的品格。
由于父亲一生极爱整齐干净,不但自己穿衣一丝不苟,还能让瘫痪床上四年的爷爷经常穿戴整齐,能有尊严地活着。而当自己身患偏瘫后遗症后,却以极大的毅力,去克服身手的不便,保持着自己日常的早起习惯,独立穿衣洗漱如厕,房间床上干干净净,甚至还分担了母亲的辛劳,用拐杖一点点地划拉聚拢着院子里的落叶,保持着一个不大的农家院子的清爽,这让先后来家里看望父亲的亲朋好友们吃惊与钦佩。

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秋,父亲患病后的照片。 供图:伊汀
父亲患病后一直住在旧宅老屋里,尽管有我的兄嫂侄女们轮换照应,但日常还是依靠身体孱弱的母亲来照料生活起居,我每次周末从洛阳回家,都要和他们住在一起两三天后才回城上班。每当清早起床时,父亲不让别人给他穿衣系扣,自己也很有耐心地用一只手,把里里外外上衣的扣子一个不落地扣整齐,衣服拽平整。父母坚决不让我们再买新衣服,晚年他的穿戴,许多都是我们自己换下来的旧制服,因缀有塑料扣子,这样比他过去穿的对襟布扣黑夹袄显得“洋气”些,父亲很是满意。
有两次我带着相机回到家里,一次正逢夏季,一次是中秋,我分别给父亲、母亲照过两次相。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彩色胶卷带得不够多,可惜只顾给左右邻居和孩子们照了,反而没有留下一张与父母的合影,这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们一生的憾事。
在农村的几十年,父亲过去几乎没有照过相,尽管腿脚不利索,照相前,他还是不让我们给他整理衣服,而是自己很认真地整整扣子,提提上衣领子,拉拉衣角,还把风紧扣都扣上了,这让外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偏瘫后遗症的老人。
面对镜头时,一个干干净净的老头,端正地坐在藤椅上,面对面就是他的三儿子。此时,我看到了一个深深镌刻于记忆中的晚年父亲,他从容微笑,满脸慈祥,他一生虽辛劳贫困,却坚韧不拔,一直执着于爱美自爱,在他时日不多的夕阳岁月里,他毫无愁容,灿然幸福。这一刹那的定格,让我永生难忘。
有人说,生活处处有美学,巧手用心是艺术。回忆父亲爱生活、爱劳动、爱家人的点滴往事,我深以为然。
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斯人远逝,留住前人的“根”与“魂”,方有家风的“精气神”。人生就是一幅慢慢展开的大写意国画长卷,父亲求真爱美至善的一生,在儿女们的心中,留下了用勤劳之手精心描绘的生活工笔画,父亲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人生美学家、生活中的艺术家。
2024年8月30日晨
编辑 郑艳艳 审校 郭建华 二审 刁瑜文 三审 张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