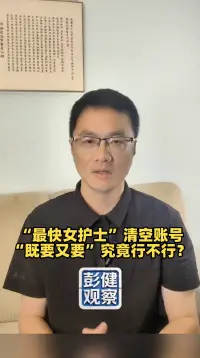要问,有生以来,对哪种鸟的鸣声印象最为深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布谷鸟。
为望帝化啼血杜鹃的传说掬泪,读文天祥绝命诗“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而热血沸腾,那是以后的事,此前的16岁,已被布谷鸟迷住了。
那是刚刚从童真的蒙昧苏醒的年华,读高中一年级。四月,学校照例放农忙假。我的家本来在小镇,开的是文具店,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的家庭分为两部分:祖父母、父亲、姐姐、我和一个弟弟是城镇户口,母亲和三个弟妹是农村户口。这个农忙假,我没留在小镇,回到母亲所住的村庄。母亲生性寡情,且患强迫症,对儿女从来不表露爱意,然而,这段日子,她对我的好,教我铭记终生。每天,我在生产队出勤,她做我爱吃的菜,向我诉说她15岁出嫁时的笑话。别小看这母性的温柔,它催生了一种情愫——对爱情的憧憬。
岭南的春天,微雨纷纷,燕子低飞。我和社员们一起去秧地把稻秧拔下来,挑到水田去插。日头隐在朦胧的天幕,白色天光落进汪汪春水。犁耙稻田的水牛在远处,影子绰约,把驭手粗野的吆喝衬得更清晰。弯腰插秧不算苦活,但腰酸且疼。歇工时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裤子粘泥浆也不管。这一刻,连老榕树也模糊的远处,咕咕,咕咕,如云块飘来,后一声追着前一声,沉着,坚忍。我悚然,问旁边的伙伴阿光:“是什么?”他斜眼看我,淡然道:是“各耕各锄”,怎么啦?这一提醒,让我记起小学课本里的诗句:“子规声里雨如烟”,我说:“学名该是布谷吧?”他没回答,低下头使劲把粘在小腿的蚂蟥扯下来。后来,从书中知道,这是四声杜鹃。
咕咕,咕咕,刺破心扉的啼唤!我的心本已敏感过度,尤其是这个春天,个子猛窜,上星期还合身的裤腿,忽然短了一截。早上醒来,仿佛听到体内有冰川崩解,冰块跌进流水的响声,那是血液的流动。鸟声中,一个巨大的五味瓶于心间蓦然爆裂,把难以名状的悲喜释放,教人不知如何是好。此刻更是,我站起来,听任身上流下泥浆,回到稻田中,飞快地插起秧来。还在休息的男女社员惊讶地看着我,阿光干脆出言讽刺:“学生哥连工分也没得拿,偏是最积极的,想拿个好鉴定是吧?”我没有答话,泪水吧嗒落在秧苗上。
我边插秧边梳理情绪,是啼声教我想念一个人。她是同校的姑娘,低我一级,以窈窕和美貌死死地吸引着我,我一离开课本就为她走神。可是,别说不敢表白,连对自己也不敢承认。无望的单恋,把“咕咕,咕咕”翻译为“苦也,哥哥”,“想你,妹妹”。
六年过去,其间我从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卒被选送为期半年的师资训练班。该班开学之初,去山区开荒一个月。又是春天,遍野是茸茸的黄色花,开在龙眼树林子。路旁是充满暗示意味的杜鹃花。要命的布谷鸟声追来,咕咕,咕咕,又缠缠绵绵地想念起她。她也是知青,从没通音问。折磨人的愁绪,让布谷鸟唱出去:你在,哪里?不如,归去。
出国以后再也没听过布谷鸟叫。回国的季节不对,也无法重温。从《随园诗话》读到清人薛立中的诗句:“应是子规啼不到,致令我父不还家。”顿时脑中嗡一声,书从手中跌落。写游子的离恨,写刻骨的亲情,它臻于不朽了。怪不得引它的袁枚赞叹:“就一时感触,终成天籁。”
编辑 温静 审读 韩绍俊 二审 王雯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