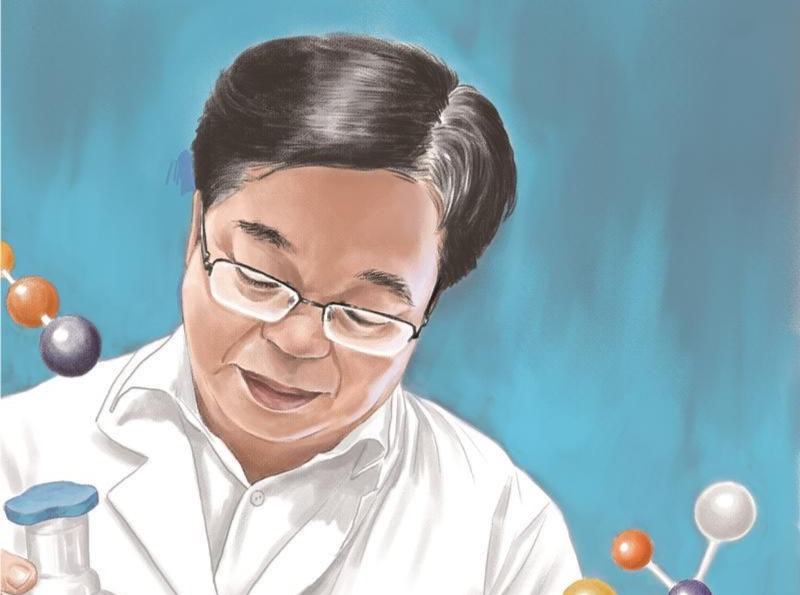“摄影,对于全世界各个不同种族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无需翻译的语言。如果说画笔是仅仅属于画家的,那么,照相机则是属于大众的工具”,这是1984年诞生在深圳的《现代摄影》杂志第一期开篇第一段。
没有人想到,这一期杂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摄影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独特瞬间。人们更没有预料到,这之后的十年里,它以先锋姿态记录着特殊的时代影像,发掘了韩磊、肖全、杨延康这一批新时代摄影人的同时,经由《现代摄影》的译介,马克·吕布等一批国际摄影大师也进入到中国摄影师的视野。
今天是“世界摄影日”,从胶卷相机、数码相机,再到如今人人都能拍摄的“手机相机”,摄影已经成为一种“全民艺术”。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38年前在深圳诞生的《现代摄影》所带给我们视觉和观念的洗礼。
在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的资料箱里,500多封手写信件记录了《现代摄影》从诞生到改版的整个生命史。

近千封寄到桂园路13号的信
其实,关于《现代摄影》的采访原本一个多月前就已完成了。但我心中总仿佛有什么事情还未做一样。
6月底,我打电话给远在北京的李媚,请她回忆38年前来深圳参与创办《现代摄影》的细节,作为杂志的灵魂人物,李媚已退休多年,她说:“我现在记忆力不好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我能想起来多少就聊多少吧。”
那天上午,我们通过无线电波,穿越时空,一起回忆了38年前一本诞生在深圳的杂志的故事。这本杂志比我还要年长,很多名字我要借助百度才知道他们是谁。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总在试图回忆和重构,这本先锋杂志的样貌以及当时在中国摄影界的震动。但总归是太久远,凭借网上的资料和李媚的口述,我还是有种够不着的感觉。
想起李媚在电话里最后对我说的:“关于《现代摄影》的所有书信往来,我都给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托管了。”
8月16日,我开车来到清水河的越众历史影像馆,馆里很久没有展览了,正门没有开。上一次来馆里,还是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2019 年起,“侯奖”这个由中国民间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接力棒,正式从侯登科生前好友、“侯奖”发起人李媚和于德水的手中交予越众历史影像馆。自此,这一当前中国摄影界重量级奖项正式“落户”深圳。
同样交予越众的,还有李媚保存多年的有关《现代摄影》的书信和杂志。
从红色的后门,上到二楼办公区,两大箱信件已经摆在桌子上了。近千封书信,还没有整理过,信封的收件地址都是清一色“深圳市桂园路13号2楼《现代摄影》编辑部 李媚 收”,寄件地址则来自云南、贵州、广州、巴黎等天南海北。
馆里的工作人员根据我的需求,提前一天筛选出了一批可能有用的信件,并用标签题注了信件的大致内容。他们提醒我,不能拍照,只能记录。要戴上手套,因信件存放过久,直接触碰可能引起过敏。
我坐下,拿起信封,小心取出里面的信纸,那信纸的叠法和难以辨认的手写笔迹都在提醒着我,写信曾经是多么具有仪式感的事情,一如当年的摄影,也曾是一种庄严的仪式。
这些信的内容一下填满了我这一个多月的空落。我想我找到了答案,38年前的这本杂志是一群人安放理想的精神乌托邦,她的先锋和开放深深植根于深圳这片自由的土壤,她的生发是如此自然,即使只存在短短十年,她那不可复制的影响力还依然不断向外辐射着。




▲创刊初期的杂志封面。
被一台尼康“拐”来了深圳
1984年8月29日,云南省新闻图片社的吴家林给李媚写了一封信:“终于在昆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现代摄影》第一期,作为多年来一直幻想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一个别开生面的摄影艺术刊物的我是不同寻常地激动。值得高兴的是,《现代摄影》有别于过去中国大地的摄影艺术刊物,且颇有点现代味,这确是一个不简单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这个良好的开端使我看到了即将获得繁荣获得百花齐放局面的中国摄影艺术。这是摄影界基本群众之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吴家林如今已是国际知名摄影师,那年的他只是云南一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工作者,他在信里提到自己在云南山里拍摄的“感觉挺不错”的照片,多年后,《云南山里人》系列作品成为他的代表作,影展开遍了纽约、德国等地。
云南,也是李媚与《现代摄影》结缘的初始地。
来深圳前,李媚在贵州安顺文化馆搞摄影,还拿了全国妇女影展金牌和铜牌奖。1984年元宵节,摄影家协会系统在西双版纳开年会,李媚作为贵州代表出席,遇见了来自深圳摄影协会的苗小康。
“那时候,深圳摄影协会是全国最富有的摄影协会。借着毗邻香港的独特条件,全国各个摄影协会的相机、胶卷很多都是从深圳摄影协会采购的。相机经营是他们的一大主要业务。”
苗小康一见到李媚,就力邀她来深圳一起办摄影杂志,“我当时挺犹豫的,因为我正是创作高峰期,我不想办杂志,我想拍照片。苗小康就说,你要去了深圳,可能一两年你就能挣一台尼康相机。我们那个时候太穷了,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多块钱,相机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李媚就这么答应了。
苗小康离开云南前,丢给了李媚一台尼康相机,对她说:“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相机吧?那留给你拍吧。”李媚一下子大受震撼:“我从来没去过深圳,对深圳一点都不了解。一台相机对我是天大的事,他就这么留给我了,这是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32岁的李媚,就这样只身从贵州南下深圳。
“那个时候的人挺单纯的,就是去做事,至于生活怎么样,适应不适应,要不要带点啥吃的,什么都没有想过,就带了几件薄衣服。我也没想过我要留在深圳,就冲着那个相机去的。”
到了广州火车站,李媚傻眼了,没有人接,“我慌了,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广州站人那么多,觉得挺恐怖的,给苗小康挂了电话,他让我坐车到深圳。”在火车站睡了一夜通铺后,李媚又搭火车到了深圳站,出了站,“还是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是心里边特别毛,心想这是个啥地儿,在云南那么热情,现在连个人都见不到。”
电话里,苗小康又告诉她,一直往前走,就到了。李媚有点崩溃:“我当时真的是想干脆往回走了,但想想,回贵州,也很麻烦,就硬着头皮走到了老街附近那个门市。”
见到苗小康,“他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热情地说:李媚同志,你终于来了!”
还没来得及感受深圳6月的炎热,李媚就投入《现代摄影》的编务工作了。

▲诞生在深圳的《现代摄影》以先锋姿态记录着特殊的时代影像,发掘了一批新时代摄影人的同时,马克·吕布等一批国际摄影大师也进入到中国摄影师的视野。
一本定价1.9元的天价杂志
《现代摄影》第一期杂志,是诞生在地板上的。苗小康等几个人选了几张照片,在地板上简单排列了一下,就有了杂志的雏形。但在李媚加入之前,没有人知道一期杂志的出版流程是怎样的,甚至连刊号都没有。“当时这一群人只想着干就完了,完全想不到有出版规定这方面的事情。”
“我因为在《大众摄影》干过半年,对版式知道一点,调整了一下图片的比例,当时也没有卷首语,我就写了一个,看稿子有点弱,又加了点稿子放在里面。”
拿到刊号,第一期在1984年7月刊出后,立马成为摄影圈里一件大事。与当今凡事都要搞一个论坛,请一群亲朋好友前来捧场点赞所不同的,那时的热情是自发而真诚的,各地的摄影师甚至自发上街售卖。
当年8月23日,贵阳日报社的王亚新给李媚写信:“昨天我和毛琦孙小波在街头叫卖了4小时,卖出了18本。‘太漂亮了太精彩了’,几天前,分会打来的电话里,我听到毛琦兴奋得跳起来。小波和我们贴了广告卖了刊物后,口口声声‘精神上获得了许多’。刊物没有说教的痕迹,确有探索创新精神。内容形式丰富,显得真挚勇敢。”
9月5日,摄影师李晓斌给李媚写信:“前几天我收到刊物时非常高兴,并且用了一个下午时间细读了3遍,可以说一个字也未放过。总的来说非常好,我认为比《中国摄影》办得好,比《大众摄影》也好,在目前来说这是不容易的。”
李晓斌在信中列了3条《现代摄影》的优点,提到不足和改进之处,他列了足足17条,其中有两条是针对这本刊物的价格:
“价格高,在内地无人敢买,要考虑全国发行,价格最好在1-1.5元之间。”
“增加相机广告,减少价格。”
这本定价1.9元的杂志,在当时普遍定价在1元以下的杂志中间,可以说是天价了。李媚说,“我们开始想得挺好的,开一个冲印店,卖相机,后来做印刷,想用这些事情支撑杂志运营。可能刚开始不赚钱,但到了一定的发行量就能赚钱了。”
事实上,这不是一本按规律做的杂志,达不到邮局的定期出刊要求,无法进入征订系统,只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跑报摊。
李媚带着几本杂志去了北京,诗人杨炼想,中国美术馆附近应该销量不错,便带李媚去了美术馆附近的报亭,“当时经商卖东西,在我们内心还是特别有障碍的”,李媚硬着头皮过去,几番交谈后,双方互留了地址,就算达成了口头协议,就这么跑了几家报刊亭,谈妥了一部分发行。还有一部分靠的是武汉、南昌等地的摄影圈朋友来代销。
第一期好评如潮,印的1万本很快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下子很膨胀,就把第一期再版了1万本,还在封面写上‘再版’两个字,我想这期杂志真的是值得保留的,因为它是一群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创办的。”
第一期印了2万本,第二期印了4万本,李媚至今都能回想起苗小康拿着计算器算账的情景,他说,“李媚同志,第三期印6万本,第四期印10万本,按照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很快就成‘万元户’了。”
但最后,所有的钱都没有赚回来。
多年后,李媚回想起她在香港见到办杂志的“大腕”施养德。施养德问李媚:“你们的广告客户是什么层面的?”李媚无言以对。施养德又问:“你们办杂志为了什么?”李媚说:“当然是文化理想,这还用得着说吗?”
《现代摄影》的成功依靠的就是这份文化理想,也有赖于改革开放初期自由开放的环境,视野、思想都先行一步,没有太多禁忌。凭借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过了罗湖桥,便是最前卫的国际资讯。《现代摄影》译介了大量国外摄影理论和作品,如今在摄影圈内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初都是聚集在《现代摄影》旗下的新锐,或曾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第一份重要作品,或曾在这里首次接触西方的摄影理论。首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摄影师刘香成就在《现代摄影》上发表过许多重要作品。
纪实摄影先锋人物张新民说:“它的办刊理念、意识主张,都是跟当时的深圳一脉相承,就是包容、开放,吸收西方的现代理念。”
虽然,彼时人们并不懂得如何将其市场化,理想无法与经济规律抗衡,但它就诞生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它像“乌托邦”一般的存在,吸引着无数艺术青年前来投奔。

▲李媚和丈夫范生平在《现代摄影》编辑部。
编辑部就像一个家
1986年,《现代摄影》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摄影“真实性”的大讨论,讨论面涉及之广、影响之深,不啻为中国现代摄影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90年代以后,《现代摄影》推出被称为“中国新锐摄影家”的新一代摄影人,在中国摄影的风口浪尖提出一个又一个具有宣言意味的口号。
1989年,韩磊从工艺美院毕业后来到《现代摄影》做设计,从这时起,《现代摄影》才算正式有了设计。韩磊说:“我当时在那里工作,至今回忆起来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不真实感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拥有的纯粹和专注。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摄影师背着自己的作品过来。李媚都会非常有耐心地接待。”
1984年底,文艺青年杨延康跟着一辆拉厨具的货车来到深圳,在深大旁边的一个面馆做了面点师,他是李媚的老乡,在贵州安顺时曾听过李媚讲课,那时李媚是安顺文化馆的馆员。
刚好《现代摄影》需要一个发行员,杨延康就被李媚招了进来。说是发行,其实就是抄订单,到了寄杂志的时候,各地的订单都是一个信封一个地址地手抄出来的。“《深圳青年报》《深圳法制报》的好多人比如吕贵品、徐敬亚、宫瑞华都帮我抄过信封。”李媚回忆道。
“我没有学过摄影,是我的导师李媚让我从一张张来稿照片中认识了摄影。”杨延康说。没事的时候,李媚总会给杨延康指导一下拍摄。有一次去连南采风,杨延康带回了几张照片,李媚眼前一亮,告诉他“我觉得你很有天赋。”李媚将他的照片发表在《现代摄影》上,这在当时对杨延康是莫大的鼓励。如今,杨延康已成为蜚声国际的摄影大师,他还是经常对人介绍:“李媚是我的摄影老师。”
为了补贴杂志的运营,编辑部楼下开了一家影楼,接拍商业照片。1990年代,肖全、卢现艺、亚牛都曾是影楼的摄影师。“肖全年轻时候很帅,又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一定要客户长得好看才有感觉。我常说他‘你不能拍每个人都得谈一场恋爱’。’”后来,肖全凭借《我们这一代》闻名海内外。
1993年,亚牛在上海读设计,他很喜欢《现代摄影》,暑假时拿了一本在学校拍的作品集来到深圳给李媚看,李媚觉得挺对路的。那时候韩磊已经离开,毕业之后,亚牛就来负责设计,也在影楼拍拍商业图片。
亚牛说:“假如把《现代摄影》比喻成一个点,大家聚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来了之后回到各自的地方,西安也好,河南也好,或者贵州也好,他们又带回去了在这里感受到的东西。”
多少年之后,有人在重溯《现代摄影》的故事时会将其看做一个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一本杂志。但在李媚看来,她并没有想那么多,她常常邀请编辑部的人到家里吃喝玩乐,看书听音乐,看外国摄影画册,“我们杂志社里其实一直家庭气氛蛮浓的,大家都觉得挺像一个家的,兄弟姐妹一样,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外地人,所以我也比较理解那些到深圳来的小孩。”

▲《现代摄影》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摄影“真实性”的大讨论。
如果不是因为深圳,这本杂志绝不可能诞生
1989年9月20日,湖北省文联的彭德给李媚写信:“我的一位朋友经常向我借书,有借有还。有一次她一口气借走我的6本《现代摄影》,从此便不打照面。我决定同她绝交。一问,6本杂志辗转借给一位名人,而这位讲信誉的人居然坚持不还,并无视她同他断交的威胁。我的愤怒于是变成了同情,为一套好书,好名声也不惜抛弃。不过,好书同好人一样,易遭误解,易受磨难。”
因为种种原因,《现代摄影》常被批评,写检查成了常有的事,甚至培养出侯登科等写检查的高手:“侯登科、石宝秀就很会写检查,每一次只要写检查,我们都会找他,他会给我们写能过关的检查。”
到1994年,《现代摄影》杂志在它最耀眼的时候戛然而止,改版为《焦点》,“当时我们渴望办一本公众杂志,渴望通过图像进入公众传播,但在努力之下,梦想没有成为现实。”
《现代摄影》停刊后,它曾经倡导的纪实摄影开始席卷全国,它所辨明和开拓的潮流,也引导着之后的摄影师去践行摄影参与社会的方向。
李媚说:“如果不是因为深圳,这本杂志绝不可能诞生。”近40年后,我们在重新肯定这本杂志失败背后的价值时才明白,它就是城市在那个时代的印记。
文/晶报记者 谢晨星 插图/淡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