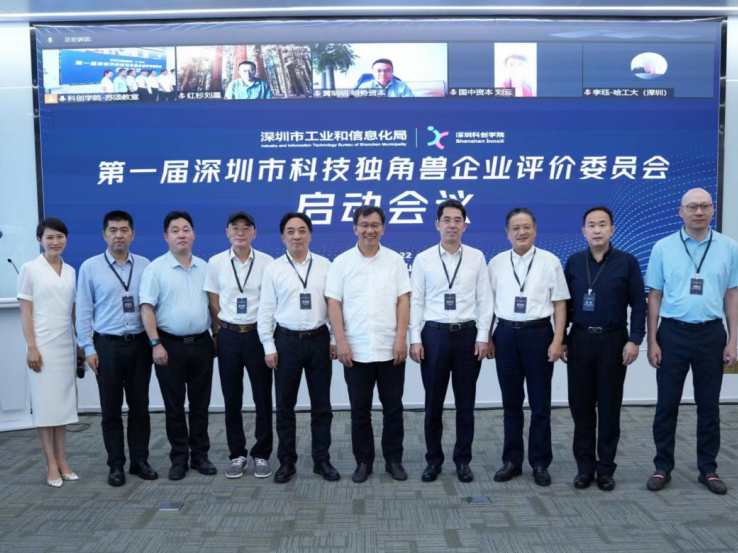艾轲便朝他的卧室走。顾濛开门进到自己的实验室,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备用的笔记本电脑,出来时又将门锁带上。这时艾轲也拿着衣服走出卧室,顾濛示意他直接将衣服送到淋浴间。
“测试是必要的。”艾轲低声说。
“不会影响你工作吗?”
“一起做,一次过,这样更省时。”
阿桑穿着艾轲的一身休闲衣走出淋浴间,他们直接将他请进艾轲的实验室。顾濛也将阿桑的双肩包拎进实验室,将它放在门口的一角,她又让阿桑坐在一把带扶手的高靠背皮椅上。阿桑好奇地看着身旁的导线和仪器。
“这是要测谎啊!”阿桑的情绪有些抵触。
“是,也可以说不是。传统的测谎是以提问为主,被测者只需回答‘是’或‘不是’,咱们却不是这样,咱们是以你说为主,我们提问为辅。”顾濛的神情温和而又严肃。
“你不妨当作是一种分享,我们分享你的真实的想法。这是合作的前提。”艾轲补充道。
“你也是在分享我们的技术,你应该这样想。这款测谎仪该是国内最领先的技术了,这是艾总的技术。用不了多久,这项技术就会变成手机上的一个小程序,我跟你说话,我打开手机上的这个功能,就会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顾濛这话立时就有效果。阿桑朝艾轲望一眼,眼神中便有尊敬的意味了。
“喂,年轻人!要想有出息,就该多一些体验。”
阿桑咧嘴笑笑,神情已变得放松了。
顾濛麻利地用皮带将阿桑的头部和上身固定在皮椅上,又往阿桑身上连上线,这些导线连着心律测试仪、皮电测试仪和脑电扫描仪。阿桑胸前、右腕及左手的两指都被连上了传感器,这些传感器通过导线连接测谎仪主机。顾濛又拿起一个有导线的头盔。这个头盔是强力电磁体,其内侧是塑料线圈。
“还要戴头盔?新鲜……”
“没见过吧?这也是艾总的改进和升级。”
“这主要是测什么?”
“脑电。头皮会有些刺激欸,就当是在给你梳头,你就当是在理发店。”
顾濛轻拍一下阿桑的肩膀,就给他套上头盔,并使头盔的内侧紧贴他的颅骨。
“放松哦,一定要放松!这不是测谎,咱们只是聊天,边聊天边梳头!但你若说谎,机器就会有显示。”
顾濛拉过一张椅子放在阿桑对面,她在椅子上坐下,与阿桑保持适度的距离。与此同时,艾轲在墙边的主机前坐下,他打开显示器开关,屏幕上便出现了多条微颤的曲线。
“就当是在跟我聊天,就当我是一个记者在采访你,但不要当我是美女记者哦!不要有多余的心跳,所以你不必盯着我看,你可以闭上眼睛跟我聊,甚至也不必当我是女记者——当作知心姐姐好了!……能做到吧?”
“我尽力配合。”
阿桑轻轻闭上眼睛,身体也摆出舒服放松的姿势。
“OK!开始吧?”顾濛朝艾轲望一眼。
艾轲点点头。顾濛便以平静的语气与阿桑对话——
“今天不是个好日子,看你那一身雨水……说说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对于他们来说,一切正常……”
“他们是谁?”
“我找过他们,不只是今天。这些日子,我想找他们作个证,举手之劳……可他们没人管……”
“作证……那天你在这海边找那女人,是为同一件事吧?”
“你是死是活,他们不管。说实在的,我父亲本是有恩于他们,其中有两个人,当初还是我父亲将他们调来的。如今可是好,他们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阿桑忽然有些激动。他睁开眼睛,愤怒地直视前方。艾轲面前的电脑上,几条曲线有有明显的波动。这些曲线显示出阿桑情绪的波动,呼吸、心律、血压、脉搏、脑电……
“一个人给单位干了一辈子,任劳任怨,埋头拉车,只靠业务吃饭,因为没靠山,你再优秀也没用。……这也没什么,有份稳定的保障就好,可是临到退休办手续了,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企业编!”
“哦……原来不是吗?”
“好多年都一直是事业编,父亲是机电工程师,三十多年前他是作为人才调来,而且是组织部调干,事业编制。可是待到退休,才突然发现事业编变成了企业编,才发现二十多年前发生的变动,自己完全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不知自己早已被打入另册,早已被划到体制外了……”
“还有这种事……”
“父亲就在公司大楼里上班,人事部的人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食堂里吃饭也常碰到,但是没人告知,没人多说一句话……”
“喂,他们不知是违法么?不是有个什么劳动法么?”
“他们当然明白,起码有个知情权的问题。事情可能是更复杂,那些有背景的人,譬如那些官太太们,他们当然不会被改成企业编……”
“毫无疑问,知情权是被侵犯了,而且是恶意侵犯。那个编制也许是被挪用了……”
“很可能是这么回事。人事处成了保密处,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谁是事业谁是企业这样的名单,员工身份成了秘密……他们也可以暗中做手脚,而员工都是老实人,他们相信组织……”
“Oh my God!身份成了秘密!……倒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东北某地搞‘厕所革命’,环卫局招几个公厕管理员,结果有数千人报名,其中很多是研究生!还有武汉招公厕管理员,明确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因为这是事业编。”
“这些事你都记着?”艾轲的语气略带讥讽。
“过目不忘,也是没办法的事。”顾濛微微一笑。
阿桑却只是深陷在自己的情绪里:“没人管!他们说这是工作疏忽,当初应该告知个人,但这是历史问题,肯定改不过来了,因为事业编市里早已冻结了。摊上了,你就自认活该倒霉吧!”
“可是单位总该想点办法,给些补偿也好。……他们单位效益好么?”
“国企,他们的日子永远不会不好过,因为有地皮,随便盖几座大楼就可以享受几十年……”
“单位只是推诿不管?”
“新官不理旧事,都是打官腔。我问人事处——后来改叫“人力资源中心”了,我问那个张主任,当年是她经手这事,你知她说什么?她说谁能看得透啊,当年我们是想为单位省点钱,社保就给他按企业账户缴了,谁知现在退休金差别这么大!形势咱们谁也看不透,就好比这房子的事,要是能看透,早些年多买套房子,一辈子就不用上班了!……你拿知情权说事,她就说,我们也是好意,好事及时告知,不大好的事就不好意思告知。你要再追问,他们就会说你要向前看,将来企事业社保肯定要并轨……可是,像我父亲这种情况,还有将来啊……”
“不可以走法律途径吗?”
“法律?……我也想到打官司,也有足够的证据了,包括单位领导和人事处的,文字和录音都有,这是事实。这些日子,我找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能作个人证,哪怕只是一行字、一句话……可他们一毛不拔。那天在海滩上,看见他们的幸福生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就是,他们要自己活得好,但不希望别人也活得好,他们幸福一定要别人倒霉来陪衬……说到打官司,我们虽是有理有据,可法院是局级单位,我这被告也是局级单位……”
阿桑沉默不语了,他的神态显得很疲惫。顾濛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她起身给阿桑倒了一杯水。
“总会有希望的,你不可以灰心……”
“不再有希望了……有了这样的打击,父亲感到一生都失败了。60岁退休便因此而郁闷,63岁便生了大病,今年也才65岁,刚在医院做了大手术,此刻还躺在医院里……有时候我也想,人家不给解决,那就自己解决。他们单位有个司机,他就不管这一套,他为一点小事受了委屈,便拿着菜刀去找老总,事情便立马解决了。……有时我也很佩服这种人,可我做不出来……”
阿桑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便感到有些难为情,便闭上眼睛。静默片刻,他又开口说话,带着一种故作的爽朗。
“我不该啰嗦这事,浪费你们时间了!这事我也想开了,注定没希望的事,就必须想开,必须认命,必须放下,悲剧就悲剧吧!……看看,我也是佛系了!”
阿桑喝了一口水,便闭上眼睛不说话了。然而,他最后的这几句话却是显得很异常,测谎仪显示屏上的几条曲线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一直沉默不语的艾轲这时站起身来,他朝阿桑走近几步。
“悲剧……人生刚刚开始,说佛系就佛系了……”艾轲忧虑地望着阿桑,“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这就算是在说谎了,可是机器不会说谎。”
阿桑像是条件反射地睁开眼,他怔怔地望着那显示屏,有几条曲线在剧烈地波动。
“既然是不甘心,就不能轻言放弃。”
艾轲的语气异常严肃,像是在训话,阿桑不由得坐正了身子。
“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了,虽然医保有限,但是房子卖了,治疗的钱也还是有……”
“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这关乎生命尊严。我也现身说法吧!我坐了两年冤狱,是外地一个偏远地方企业和法院——基层法院害了我。我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应是有一大笔钱。我需不需要这笔钱?有这笔钱当然是好,没有我也能过下去。可问题是,按照相关规定,这样的国家赔偿要由办错案的地方法院来出,也就是地方财政。地方财政也是穷,尽管县乡政府都有豪华办公楼,那却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教师工资欠着,孩子赤脚上学。那么这个钱我要还是不要?我跟我的律师说,必须要!是的,这关乎生命的尊严。要回这笔钱,我定会以可靠的形式捐回去,捐献给当地的学校,为那些留守儿童,我是指望那些赤脚上学的孩子能有更好的教育,待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假若他们能读大学,假如他们中有人将来成为法官,那么就有可能是有良心的法官,也就不会因为贫穷的原因而害人……”
“哇!敞开心扉了!”顾濛激动地拍起手来。艾轲和阿桑都望着她,因为她鼓掌的动作太夸张。他们看她的眼神有些怪怪的,这使她感到自己像是个疯婆娘。意识到这点,她忽然就脸红了。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