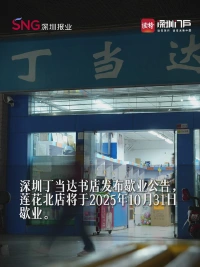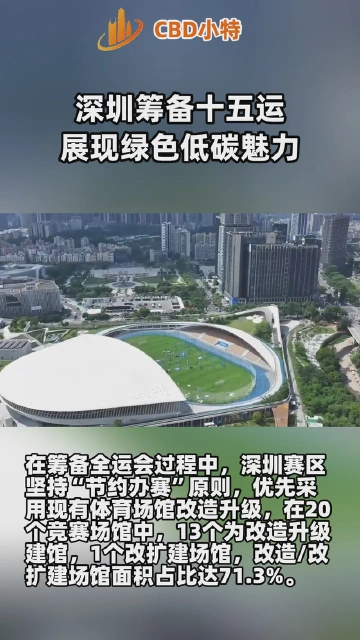原以为,屈原过后,再无来者,没想到一百多年以后,贾谊来步他的后尘了,但没有跟他一样去投江,而是做了一篇《吊屈原赋》。
楚人一旦遭遇大忧,就爱唱歌,从屈原开始。班固释《离骚》之“离”为“遭遇”,司马迁注《离骚》之“骚”为“忧”,合二人之说,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大忧”。屈原遭遇了大忧,便唱出了《离骚》。
楚人还善感,百感交集时亦好为楚歌。“刘项原来不读书”,可都爱唱歌,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千年等一回的好歌。天放之人,发为天籁之声,直指天命。
《垓下歌》仅二十八字,便将英雄气概和儿女情怀以及对天命的感慨,都表达出来了。试问后世诗人,谁有如此大气派?《大风歌》只三句,就将帝王踌躇满志和内心深处的焦虑,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对这样的诗句,王夫之只好叹曰:岂亦非天授也哉!
有人说,鹰击长空从来不唱歌,唱歌的都是被鹰抓捕的小雀。项羽破釜沉舟,决战章邯时,没有唱歌,在十面埋伏中却唱歌了。还有那位深得“骚体诗”真传的洛阳少年,他叫贾谊,被贬到长沙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活着的屈原,整个朝廷都跟他作对,他做了一篇《吊屈原赋》,一面凭吊屈原,一面为自我立言。
原以为,屈原过后,再无来者,没想到一百多年以后,贾谊来步他的后尘了,但没有跟他一样去投江,而是做了一篇《吊屈原赋》,在精神上与他共鸣,这一鸣,虽然没有实际行动来作证明,但还是惊艳了太史公,没人比太史公更理解更同情那一鸣了,所以在《史记》里,就将这两位相隔了一百多年的知音合为一传了。
洛阳少年凋零后,大汉迎来了一位少年天子,刘邦的曾孙,汉武帝刘彻。刘彻也是一位诗性少年,与洛阳少年一样,都有一份婉约的心肠,都能感受到“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情绪分量。但两位少年的性格却不太一样,贾生以婉约入忧郁,而有抑郁症倾向,少年天子则是正常的青春期的惆怅,仅以婉约表达他淡淡的哀伤,虽不似贾生那般刻骨,却也沁人心脾: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摇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便是少年天子的《秋风辞》,他不作苦人语,也不带萧瑟意,隐隐“哀情”。愁是青春期的感受,有一种对诗与远方的迷茫与无奈和不由自主的感慨,如春之花儿初放枝头,等待来人喝彩。
在秋风白云、花草美人、楼船歌舞的欢乐中,少年天子箫鼓齐鸣,意气风发,但好诗要沉郁,于是,少年天子忽生天纵我材、时不我待的感慨。
《秋风辞》之于汉,一如《春江花月夜》在唐,都有一种王朝开国时的青春理想和壮丽景象,并以此来唤醒美的人生,理想在欢乐中略带一点淡淡的哀愁,才有美的格调,才能激发群体飞扬。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秋风辞》,“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题《观澜 | 汉人爱唱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