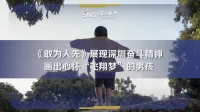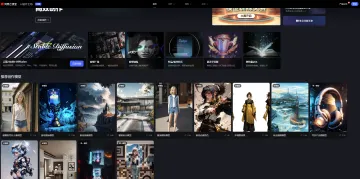《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Ⅰ》 《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Ⅱ》 [波]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 著 林洪亮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19年4月出版
我理解爱情不能理解的
希姆博尔斯卡(又译作辛波斯卡)虽然被称为抒情诗人,也享有“诗坛莫扎特”的美誉,但我们从这两本《希姆博尔斯卡诗集》发现,她并不像我们习见的抒情诗人的形象。将她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或是与现代主义时期的诗人比照,在她身上智性的成分总是占有上风。这从她写下的为数并不太多的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作,可以证明。
从气质上,她不是那种激烈的诗人,毋宁说,她更喜欢追求一种平淡却隽永、清晰却绵长的诗意。她的名诗《一见钟情》——据说催生了基耶洛夫斯基电影三部曲《红蓝白》之《红》的灵感——然而,这首诗本身,与其说是关于爱情,不如说是对于命运的沉思。诗人处理的其实是一个永恒的题目,正如马尔库塞感叹过的: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彻底消除了所谓机遇或命运的社会,比如十字路口的相遇,邂逅或错失等,社会制度再精确的设计也无法避免(见《审美之维》)。诗人在诗里说:一见钟情固然美丽,而“并不肯定”依然美妙。接受这样的现实,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说到底,所有的故事,都只能算是从“中间”开始的,如同一本故事书“总是从半中间打开”。
所以,即便是读她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诗人也时时让我们想起斯宾诺莎的警句:“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希姆博尔斯卡确有一颗富于“同情之理解”的诗哲之心,这使她在看待爱情、婚姻这样的问题上表现出超凡的冷静和高超的智慧。《微笑》一诗写得诙谐、幽默,却毫不肤浅,且颇具戏剧性的张力。《火车站》一诗也是如此,冷静的叙述与想象,体现的是道德的克制、“失乐园”的惆怅,而非人造天堂里的男女私情、情感烈焰。名诗《金婚纪念》则感叹性别模糊,婚姻中神秘感的消退,个性中差异性的一面淹没在相似性中,虽然涉及“金婚”,诗也没有落入对神圣婚姻礼赞之类的窠臼。
《感激》一诗也许更能体现作者宽阔的爱情观,因为这首诗里的第一人称完全可以视为作者自己(有时则不然,见下文)。诗人说:“我理解/爱所不能的理解,/我原谅/爱永远无法原谅的事物。”写的是多么优雅得体,深沉大度!“从初次见面到情书来往/那只是几天或几个星期/绝不会是永恒。”显然诗人绝非不相信爱情,只是她有一个更高的尺度——“永恒”,在永恒面前,实在没有什么是需要计较,是值得计较和放不下的。但诗人并未落入虚无,她仍然相信生活的真实性,相信在爱情之外、在和平相处之中,有着更美妙、更美好的爱情:“我什么也不欠他们的。”
顺便说下,米沃什对希姆博尔斯卡诗歌风格有过一个精确的评论。“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比如《回家》里的男主人公跟作者其实无关,《我离他太近了》里的“我”也未必写她自己,《墓志铭》明确是写自己,但也没有透露多少个人的私人信息,诗里只是简洁地给了自己一个概括:“一个老派的女人”、“未曾加入任何文学派别”,如此而已。希姆博尔斯卡一贯拒绝展示私人性的东西,而宁要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生活里更是如此,她严守个人的隐私),这在诗学上与艾略特主张的“非个人化”暗合,而与我们汉语文学/诗歌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似乎截然相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值得诗人们思考的。
偶尔,我们有灵魂
和抒发爱情的主题一样,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曾沉思有关灵魂的问题。自然,希姆博尔斯卡也不例外。对“灵魂”的沉思,更是经常成为她晚期写作的题目,考虑到“灵魂”(不朽)与“死亡”的密切关系,这样算起来她在诗中讨论的次数则更多。早在《在一颗小星星下》(发表于1972年)一诗里,她就以一种自嘲的语调写道:“灵魂啊,请不要指责我很少谈到你。”
她这种异常谦卑的态度,会使那种对“不朽”自以为具有十足把握的人羞愧。我想,正是在这种并非故意的谦卑里,包含着某种神性。如果我们同意米沃什所言,这是一个“后宗教的时代”,希姆博尔斯卡这样关于灵魂的态度,肯定就更显真实,也更令人信服。在最新的诗作里,还有一首直题为《谈谈灵魂》的诗,可以读到她更为坦直清楚的表述。在她笔下,“灵魂”是那样一种超然的存在,跟我们人的身体有关,跟我们有关,但也更经常地“外出不在”。“这里所谈的灵魂,/没有人能不间断地/或永远地拥有它。”换句话说,无人时刻拥有一颗灵魂。这不是今天尤其普遍的事实吗?这个事实,令人难堪,但诗人以微妙而善意的反讽道来(而且讽喻的对象并不自我排除),故而使人容易接受。对于灵魂,诗最后说:“就像我们需要它,/而我们/对它也有某种需要。”前一句好理解;但为什么说“它也需要我们”呢?这就是我说诗人在灵魂问题上更为真实、也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因为在我们不存在,在我们死后,灵魂是否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是不能被证实、当然也无法被证伪的。希姆博尔斯卡虽成长、生活于一个天主教传统浓厚的国度,但是,无论就其教育背景,还是个人思想的发展而言,或许都倾向于接受无神论、进化论这样一些思想资源,本质上,她是一个更倾向于科学精神、现世价值的现代主义者。
正是由于这样,她在写作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时,同样表现了比较理性、达观的态度。《毫不夸张地谈谈死亡》写于作者创作力旺盛、才情丰沛的时期,不仅典型地代表了诗人的风格,也很好地揭示出作者在死亡问题上的独特意识:
虽然她一再成功,
但也有无数次的失败,
无数次的击不中目标,
以及无数次的再试身手!
……
谁认为死是至尊万能的,
那他本人就足以证明,
死并不是无所不能。
无论是何种生命,
只要生存过一瞬间,
就会有永生的可能。
这首诗,也许会令人想起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名篇《死神,别骄傲》,不过希姆博尔斯卡显然让人觉得更加亲和,而较少多恩诗歌那种高蹈、玄学派风格。在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里,一切都是具体可感的;诗歌的主题,对“瞬间可以永恒”的确信,表达得透明,奇思异想均以生动而实在的细节与意象而呈现,让人不得不叹服其诗才的高明。
编辑 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