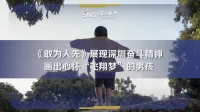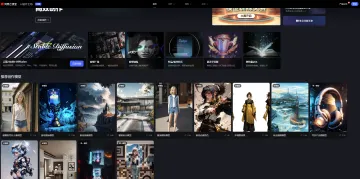《游荡者》 [土]尤瑟夫·阿提冈 著 邢明华 译 三辉图书·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帕慕克说过,他有三位土耳其文学上的英雄——阿赫梅特·哈姆迪·唐帕纳尔(1901-1962)、奥古兹·阿泰(1934-1977)、尤瑟夫·阿提冈(1921-1989),他追随这些作家的脚步而成为了小说家。这三位土耳其作家的确有着荒野上的漫游者和开拓者的形象,他们在奥斯曼帝国阴影笼罩下的土耳其实践着现代主义文学书写,让土耳其文学摆脱了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他们的代表作大多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唐帕纳尔的小说《时间调校研究所》出版于1954年。阿泰的小说《断裂》出版于1972年。阿提冈的《祖国旅店》则出版于1973年。此时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已然启程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现代主义文学写作依然是孤绝的事情。其孤绝大概可以在唐帕纳尔的《时间调校研究所》见到。小说中一群贵族、艺术家、神秘主义者创建了一个时间调校研究所,其野心是将所有土耳其的钟表调校为西方时间,土耳其在转变为现代社会时所遭遇的荒诞的困境可见一斑。的确,在土耳其写作,尤其是写作现代主义文学,必定要触及那条文明的界线,这条隐而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界线,与那道地理上分割了亚洲和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形成了幽谧的呼应。阿提冈的写作更是在这条界线上如履薄冰、毅然决然地展开。
阿提冈出生后的第二年,即1922年,存续五百多年、曾一举灭掉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覆灭了。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928年,土耳其语正式实行字母拉丁化。然而作为具有沉重传统负担的土耳其在现代化道路上不见得一帆风顺。现代与传统的剧烈冲突,弥漫在阿提冈的文学作品中,使得其绚烂复杂、秘响旁通的现代主义书写技法具有了别样的面目。
帕慕克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说过,土耳其需要发明一种现代的民族精神。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大概可以用来呈现现代民族精神的隐微的纹理与脉络。因为,按照帕慕克的观点,小说可以拆毁一元论的世界观。现代小说来源于局外人和孤独者。本雅明言道,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体。孤独的个体是阿提冈作品中的主要形象——尽管他一生只创作了三部小说:《游荡者》、《祖国旅馆》和生前未完成的《坎尼斯坦》。1989年,阿提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遗作《坎尼斯坦》只能作为残篇在2000年出版。帕慕克提到阿提冈时充满了敬仰之情,他说,“我热爱阿提冈;他尽管受益于福克纳和其他西方传统,却能够保持本土性。”换句话说,阿提冈作品中的孤独个体依然是典型的土耳其人,一个在文明界线上危险地漫游的土耳其人,就像《游荡者》里那个漫游在伊斯坦布尔街道上冒犯希腊姑娘的主人公。
阿提冈的小说里游荡着一个孤独的主人公。他有时候旁观着周围的人,无论是街道上的还是电影院、酒馆、旅店中的人,有时候则旁观着自己内在的那个自我,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两种旁观往往同时发生。在他的小说里,对自己的精神进行着分析的人,一旦试图与人交往,就处处落败,于是退避进入幽独的自我,却又甘于一味地退避,于是又带着向外的欲望走向外在世界。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始终有着悲剧色彩。现代的孤独个体想要成为本雅明所谓的“游荡者”(Flaneur),需要的是一个透明、敞开、自由的都市空间,然而,这个空间在土耳其并未全然成形,至少在阿提冈的作品中情形就是如此。
《游荡者》的主人公终日游荡在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都市伊斯坦布尔,这里曾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都城。帕慕克以温情脉脉的文字写过一本散文集《伊斯坦布尔》。在这本书中,伊斯坦布尔成为了一座帝国逝去后留下的废墟,一座充满了“呼愁”的栖居之城。在这里,人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温情、依恋,并夹杂着疏离与紧张。《游荡者》中伊斯坦布尔就是一座“呼愁”之城。主人公游弋在各种空间里,酒馆,电影院,咖啡馆,画室和街道。他甚至收集街道的名字。他与这座城市骨肉相连。然而没有一个空间可以完全接纳他。他无从安定自己的生活,身体和心灵一直行走在路上,摇摇晃晃,失魂落魄。他与这座城市之间似乎又格格不入。那位被称为“游荡者”或“漫游的人”(Aylak Adam)的主人公的生活存在着一个核心,即对“她”的渴望:“在街上,他听任冷空气充盈进出肺部,内心感受到强劲的力量。他站在街角看着宽阔的街道。行人、汽车、电车从他面前经过。路灯刚刚亮起,映照爱抚着这座城市。他一直在寻找的就在这里,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路人之中。也许今晚他就会找到‘她’了。”这是一个无名的“她”,一个看似终极却是可以随意替代的“她”。他正是在这个“她”身上,投射了无限的欲念和希望。“她”是一个引领着他行动的不可化解的他者,让他在意识中无止尽地漫游。这一点正好体现了阿提冈的小说的叙事特征——叙事流动不居,正如流动的意识。阿提冈喜欢使用括号,有时候甚至在括号中套用括号,而括号中的内容正是普鲁斯特式的“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是突如其来的回忆与想象。括号里的空间是对当下都市空间的持续消解和逾越。所以,阿提冈的小说文本一直有着溢出的旁枝末节,四通八达的孔洞,出其不意的幽径与巷道。
《游荡者》中有着意识流小说的痕迹,也有着加缪写于二战期间的小说《局外人》的影子。《游荡者》的主人公热爱书籍、电影和戏剧,却与这个城市中的人和事物难以和解,他是一个被排除出去的局外人,只能游走在人群的边缘。这截然不同于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后者置身于人群中如鱼得水、与一切现代事物形成通感、甚至感受到来临中的乌托邦的愉悦。《游荡者》中的主人公——小说过了几十页,我们才知道他叫C——在经常烂醉如泥,臭气熏天,甚至遭人痛打,似乎受到人和城市的敌对。
显然,《游荡者》书写方式继承了斯维沃、乔伊斯、福克纳的传统。然而,它对这个传统偏离和改造得不够有力。《祖国旅店》则深入了更为复杂的、纠缠着历史记忆和当下处境的空间。这一次,阿提冈撇开了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将小说设置在了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城镇。与伊斯坦布尔相比,这个城镇偏远得多。然而小说对精神的分析深入了许多。从叙述内容上看,与《游荡者》一样,《祖国旅店》依然是关于情欲的书写。主人公泽波杰特是“祖国旅店”的书记员,在某一天爱上了一个从安卡拉开来的晚点列车上下来的女人——她承诺下周再下榻这个旅馆。于是,这个女人成为了泽波杰特挥之不去的欲念的对象。她的到来一直被推延,直至主人公自杀。比较而言,这个女性他者在《祖国旅店》显得更加具体,不再是《游荡者》中的一个不在场的存在。小说这样写她:“二十六岁,相当高。胸部丰满,有黑色的头发和眼睛,长长的睫毛,眉毛稍稍修过。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脸色较深、脸孔紧致。”当然,对于泽波杰特而言,这个具体的女人终究是不具体的,他对她的爱毫无来由——也许,阿提冈试图消解的就是“爱”。爱,通过与另一个个体的结合,朝向人的整全。然而阿提冈呈现的则是一个在精神迷宫里漫游的人失去了可能与之结合的爱者,或者说,爱者变成了一个能指意义上的欲望的他者。由此看来,他对女佣泽伊的占有和谋杀大概只是欲望的移情和受阻导致的结果。

《祖国旅店》 [土]尤瑟夫·阿提冈 著 刘琳 译 三辉图书·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此外,这样一种能指化的情欲在《祖国旅店》里有着一个如帝国幽灵一般挥之不去的历史语境。《游荡者》的开头引用了16世纪土耳其宫廷诗人巴基的一句诗:“开篇精巧的寓言故事,却讲成了志怪传奇。”阿提冈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志怪传奇”,人在这个历史时代的精神传奇。不过,《游荡者》“冬季”篇第一节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到了第二节就开始转入第三人称叙事,似乎整本小说都是在解释第一节里以第一人称构筑的自我。《祖国旅店》则以“称呼语”一节开篇。不同于《游荡者》的内倾,主人公泽波杰特所身处的正是这样一个“称呼语”营建起来的外在历史空间。这个空间里充满着前帝国投下的巨大而漫长的阴影:男人贝伊,女人哈尼姆,“有钱、有地位者的称呼”;男人阿比,女人阿布拉,“字面上指‘大哥,大姐’,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表示熟络的敬称”;艾芬迪,“称呼地位较低的人时,表示谦虚的固定用语”;阿迦,“农夫中使用的最高敬语”;乌斯塔,“称呼工匠(如汽修工、水管工等)的头衔”。值得注意的是,后三种称呼中没有对应女性的用语。从这些“称呼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社会依然充满了权力、等级、性别的界限。语言一旦流散,就难以根除。正是在这样一个边界清晰的社会里,《祖国旅店》的主人公才显示出了清晰而独特的生存面目。我想说的是,阿提冈以这样的“称呼语”作为小说的开头是别出心裁的安排,是为了将小说植回到具体而错综复杂的土耳其历史传统语境里。
这些事实与小说叙事之间形成隐秘的对应关系并非无关紧要,也不会让阿提冈的小说单纯成为民族寓言的承载物。恰恰相反,阿提冈的小说与历史之间充满了巨大的张力,可以说,他通过极具欧洲现代主义小说特征的反讽消解了土耳其历史的惰性。如果说,“祖国旅店”是土耳其国家的隐喻,那么,这是一个反面的隐喻,是一个充满解构力量的隐喻。在阿提冈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自我确认的失败,身份认同的不可能,以及自我与外在生活空间的割裂与疏离。《游荡者》的主人公其实游荡在自己的内在意识里。《祖国旅店》的主人公同样如此,他游荡在自己的欲念里,这个欲念对应着旅馆空间。在这个旅馆里,他每天记录着旅客的名字,然而他并非如实记录,而是偷偷置换成无数自己虚构的名字——他游荡在一个名字/符号构筑的世界里。他也游荡在旅馆中萦绕的家族和个人记忆里。旅馆就是他的家,他的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他自己也出生在这里——六号房间。当然,他也游荡在无所凭依的、终究不可能的欲望迷宫里。
不过,相对而言,《祖国旅店》的时间要具体而集中,我们知道泽波杰特33岁,小说时间集中在他遇见那个从安卡拉开来的晚点列车上下来的女人之后的三四周里。而《游荡者》的时间要含混得多,小说四个部分分别是四个季节:冬季、春季、夏季、秋季,故事发生在何年何月终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息。但是,在时间之外,这两部小说的重心都落在了一个巨大的幽暗的精神空间。我们在卡夫卡的小说里遭遇过这样一种幽暗空间。
阿提冈的小说主人公确实呈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状态。然而,帕慕克曾说过,精神分裂症可以让人聪明。帕慕克大概是想说,精神分裂拒绝凝固的主体,而是让主体走向一个敞开的未来。阿提冈不只是要通过小说中游离、彷徨的主人公呈现生命的困境、自我认同的艰难,他不仅仅在分析问题重重的精神世界。《游荡者》中那个永不出现的“她”,《祖国旅店》中那个永不回来的从安卡拉开来的晚点列车上下来的女人,分明指向了一种未来。阿提冈的精妙之处在于,他并不提供确定的未来,而是呈送了一个难以界定、含混飘渺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小说家不正是通过书写而发明未来吗?阿提冈提供了自己的答案,惟有一个碎裂了的、一直处于漫游中的、不断探寻自我、不断受到他者邀约的个体才能通向未来。这正是《祖国旅店》具有的冒犯性和启示性。《游荡者》的主人公将对母亲的、妹妹的爱转移到了一个无名的“她”,《祖国旅店》则要激进得多,将对一个无名的“她”的欲望转移到了一个迟迟不来的女人身上。前者的欲望可以解释,后者的欲望则是空穴来风,因而呈现出绝对的自由,可以超越既定现实的约束。
编辑 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