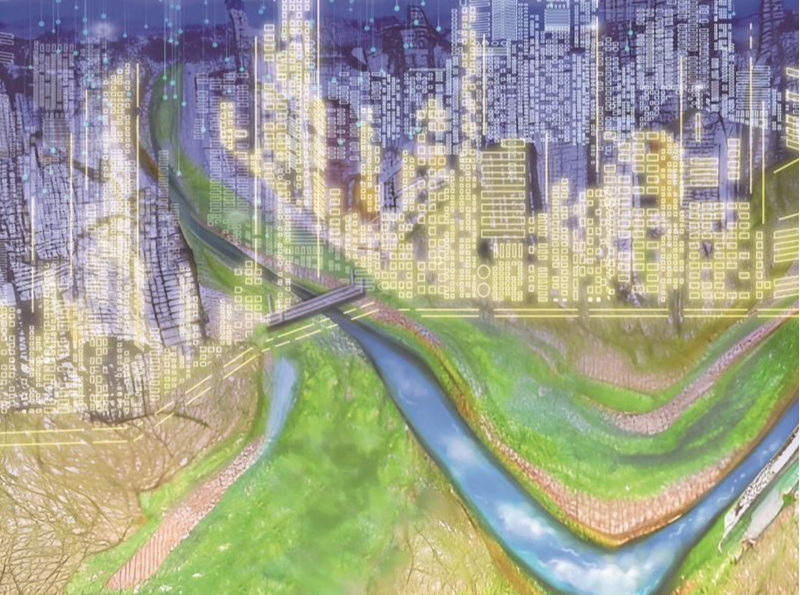不久前,有人发起了一场叫“读诗换物”的行为艺术活动,即给店家朗读一首诗歌,老板如果觉得行,就给予一定的食物。有一次,发起者朗读了深圳诗人朱建业的一首诗《染黑》,换来了店家的五张大饼。
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深圳究竟有多少人在写诗?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又如何平衡生存与写诗的关系?对城市这个文化容器来说,他们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深圳有着一个数量庞大的写作群体,有人估计达10万之众,其中又有相当部分以写诗为主。数目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说深圳一个基数巨大的诗歌写作人口,是没有错的。在深圳,众多诗人群落构成了茂盛诗歌生态,他们中有公务员、教师、医生、公司职员、个体老板、流水线打工者……以诗的名义,他们几乎占领了所有的职业身份领域。他们一方面承受着日常生活的琐碎与生存的压力,一方面近乎固执地坚持写诗,大量诗歌与“城市”“工业”“铁”“机器”“城中村”以及“乡土”“故乡”等有着密切关联。

写诗的警察、公务员
“我那首《染黑》,是有一次妻子带我去理发,师傅劝我染个头发,回来后有感而发,就写了。”朱建业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炒股不唱歌跳舞,尤其是麻将,学都学不会,平时爱和家人在一起,我的很多诗都是家人带来的灵感。”
他透露,他给孩子写了一百多首诗。

▲朱建业
朱建业是70后,法律硕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武汉读大学时就喜欢写诗,诗歌《你的长发为谁而留》曾被谱成校园民谣传唱。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先在某街道办工作,后来调入深圳市信访局。
他说,他的诗歌写作中断了19年,前些年才重新拾起诗歌,“诗歌是我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拒绝平庸的一种方式,是对自己灵魂的一个交代,如此而已。难言之隐,以诗了之;难言之痛,以诗抚之;难言之喜,以诗抒之;难言之困,以诗纾之;难言之怒,以诗疏之。”
虽然,有人拿他的诗去换饼,但他并不欣赏一些所谓诗人放浪形骸、把自己过得穷困潦倒的做派,他说,诗人首先是人,必须负起一个人应该负起的责任,不能因为诗歌而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多少人视诗人为疯子,就是因为一些所谓的诗人没有真正的诗人的样子,只是把诗歌当作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他说,他的职业很严肃,他尽量不让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诗人的身份重叠,诗歌是诗歌,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家庭是家庭,互相独立绝不干扰。
不过,他也感慨,诗人活在当代有点生不逢时。“譬如在唐代,不会写诗的人是不能做官的。但现在,如果你业余时间唱歌跳舞打麻将,人们会觉得是正常的,但如果你说业余时间爱写诗,有可能引来嘲笑。所以,你必须在保持本真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好这些因素和压力。在诗歌养不起诗人的时代,让我们用真诚和心血养活诗歌吧。”
和朱建业一样,鲁子也是在南下深圳后,才开始大规模写诗的。
读高中时,因为作文被作为范文得来的成就感,让鲁子萌生对文字的热爱。但是命运却没有如愿把他送进大学中文系,而是让他在公安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刑警。新世纪初,调来深圳,依旧做警察。和这个时代众多诗歌归来者一样,生活安顿之后,他又重拾写作。
他写过一首最能表明他的身份与心迹的诗,名叫《墓志铭》:“世上的窃贼们,当你/经过诗人鲁子的坟墓时/请你小心被抓了去/因为他在生是个刑警!”
不过,在深圳,他至少有七年时间属于抽屉写作。一个诗人何以在博客兴盛而衰,自媒体应时而起的时代,不是把每日的写作像晾晒衣服一样晾出来,而是让它们躺在抽屉里?

▲鲁子
他也曾这样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写诗是为了发表吗?”他最后告诉自己,除了对语言有足够的敬畏心以外,他把写作本身当做了禅坐,而不是为了炫耀或刷存在感而写作。也因此,那几年,他进行了恶补式阅读,包括中国和西方的大量经典。
他说他是一个深受唐诗宋词滋养的人。但他也曾在文章中罗列了他喜欢的国外十大诗人:博尔赫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伊丽莎白·毕肖普,杰克·吉尔伯特,罗伯特·勃莱,保罗·策兰,德里克·沃尔科特,罗伯特·弗罗斯特,约翰·阿什贝利。
202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警察诗人鲁子的第一本诗集《鸟舍时间树》。
在深圳,应该有不少像朱建业、鲁子这样的诗人,他们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写诗,是为了让生活变得不那么庸俗,是对庸常的一种反抗。
“环中国大陆边境线(海岸线)自驾行吟第一人”
诗人总是喜欢整点不一样的东西。
不久前成为晶报元故事主角的诗人刘美松,十几年前曾经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男子身无分文百日游中国”事件,为了检测国人的诚信问题,他一个人、一辆车,不乞讨、不打工、不要一分钱的赞助,以打欠条的方式走遍全国。100天的行程,刘美松开车行驶了28510公里,南到三亚的天涯海角,西到乌鲁木齐,东至山海关,北到黑龙江的漠河,整个行程,他总共打了222张欠条,后来以此写了一本名为《欠条》的书。
今天要说的是另一个深圳诗人,李立。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云南,“在洱海边躺几天再回深圳。”
李立是60后,初中开始写诗,高二开始主编铅印诗歌报,1989年就因为写作特长,得以进入深圳某政府机关工作,后来辗转做到深圳某国有大银行的支行行长。
但是,进入2016年,他就像一台死机的电脑开始重启一样,“到这一年,我中断写作已经整整21年了,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强烈地想要去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
为了写诗,也为了旅行,他在这一年辞了职——这在常人看来需要一定的勇气——足迹遍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留下了数百首世界地理诗,自称“地球村流浪汉”。

▲李立
当然,他更大的壮举是,2021年3月,他从广东汕头前人下南洋的始发地出发,环中国大陆边境线(海岸线)自驾环行祖国河山,有媒体称其是“环中国大陆边境线(海岸线)自驾行吟第一人”。
李立此行经过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最后在海南环岛一圈,整个行程在南海之畔的海口画上句号。其中,当驾车行至甘肃时,遇到南京机场新冠疫情反弹,他不得已中断行程。两个月后等疫情好转,于10月中旬开始,从宁夏银川重新出发,按计划完成了余下的全部行程。
此行程历时五个多月,跨越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程4万多公里,分别到达中国的最西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恰县,最北边——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最东边——黑龙江佳木斯市,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因新冠疫情防控需要封岛而未能登岛,最南边到达三亚市,最冷的地方到达中国的冷极——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根河,这里曾经录得零下58℃的全国最低气温纪录。
此次环边境线旅行,他发布了56个视频,写诗40多首,其中长诗28首,总行数达到8000余行。尤其是他的“大”系列人文生态长诗如《大戈壁》《大雪山》《大漠》《大河》《大草原》《大平原》《大都会》《大海》《大地》等,在诗歌圈引发关注。
他说,“将来有机会,还是打算沿着中国大陆边境线重走一回,牵该牵的手,走该走的路,吹该吹的风,淋该淋的雨,咬该咬的牙,历该历的险,流该流的泪,痛该痛的苦,开该开的心,相该相的爱,享该享的乐,写该写的字。”
说到特立独行,不能不提及另一个被称为“飞行诗人”的深圳诗人太阿。
几乎每隔一两天,他就会在微信朋友圈晒他新写的诗。6月30日这天,他在朋友圈写道:“六月记:一晃半年就要过去了……控制写诗,6月份还是写了11首……”后面附了一组诗。其中有一首《继承者与南方》是写给不久前去世的黄永玉的:“南方的先驱/从沈从文到福克纳/黑暗中的光/给他们严父般的教诲,给我祖父式的恩泽。”太阿和黄永玉是湘西同乡,前些年,每次去北京的时候,他都会去看黄永玉。
太阿的经历很丰富。
他大学时读的是数学系,却因为热爱写诗在大二时一度想转到中文系,“那时转系很难,校党委副书记戴海老师特批我转,但必须从大一开始重新读,于是便放弃了,毕竟我的数学又不是读不下去。”
毕业后,不愿意分配去教书而放弃了体制身份,混在省城某媒体。后来南下深圳,先在一家通讯公司就职,后来去了一家银行、再后来转战媒体,任记者站站长、新闻主编、报社副总经理。数年后进入地产行业,先后在数家大型上市地产公司担任过地产营销总经理、集团分公司董事长、集团副总裁等职。
不管身份如何变化,这些年来,对他来说一成不变的可能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写诗。工作关系需要满世界跑,无论是飞机上,还是高铁上,他都不忘每天至少写一首诗,而且是写在纸上的那种。

▲太阿
他说,通过写诗,他试图从空间进入历史,从身体进入心灵,将世界性的知识经验和时事地理景观结合到个人的现实中,以达到某种共时性状态,并在远古神话向现代神话过渡的形态中找到诗性的立意与立言基础。诗歌大多都立于当下或瞬间,或从历史、宗教、传说中来,或从建筑、自然、爱情中来,甚至“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国家”。
李立、太阿代表的是这样一个深圳诗人群体,他们在经过多年打拼后,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属于世俗意义上的金领。但他们并不安稳于一成不变的生活,在身份的不断切换中追求精神的丰盈。诗,让这样的愿景成为可能。
向劳动致敬,向诗致敬
下午六点多,拨通诗人李晃电话的时候,他还没下班,忙着在办公室整理材料。
他现在深圳龙岗区园山街道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担任《园山》杂志编辑。
李晃的名字曾经出现在1996年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那篇题为《浮出水面:深圳的文化游牧部落》的报道写到,作为酒店行李工的李晃热爱诗歌,用微薄的薪水创办了一份诗报,并请来了台湾诗人洛夫题写刊名。“勤于创作的李晃还数度被报刊推介过。尽管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处境,但这至少使更多的人知道了,在深圳的钢筋水泥缝隙,一种叫诗歌的野生植物还在顽强地生长着。”
是的,如今距离1996年已经过去了27年,李晃也由一个搬运行李的小伙子变成了中年大叔,但诗歌仍在他的内心生长着。就在不久前,他最新一部诗集《侠客行》出版了。
这些年来,李晃在不同职业领域晃动,先后做过物业管理、学校校报编辑等,飘零不定,中间还短暂地离开过深圳,但很快还是回到了这座熟悉的城市。
他有两个孩子,同在深圳的妻子收入也不高,但是,琐碎的现实生存压力之下,他一直没有放弃诗歌写作。2010年与王小妮、徐敬亚等著名诗人一起入选“深圳30年30名诗人”。

▲李晃
近几年,他开始迷上地方文史,“年龄大了,慢慢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清代以来的家乡风物。”
80后诗人袁叙田是一个看上去有点羞涩的小伙子,笑起来眼睛里有一种少见的明亮感。不知道这跟他喜欢写诗有没有关系。
2009年4月,大学毕业的袁叙田作为深圳地铁公司招聘的定向生来到深圳实习。不久后,他就和在网络认识的一帮深圳年轻诗人见面了,如程鹏、李江波、李智强、艾华林、罗益葵等。
那一年的11月15日,龙华大浪举行了一场叫“诗歌之夜”的活动,他坐332路公交车花了2个多小时才到大浪路口,然后搭摩托车到大浪会堂。那天晚上,他认识了诗人李邵平、范明、夏子、樊子、阿翔等以及一众打工诗人,觉得自己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自此后,他热衷于参加各种文学讲座与诗人聚会,宝安、龙岗、南山、罗湖、福田几乎都跑遍了。参加的活动越多,认识的诗人朋友也越多,他惊讶于深圳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和自己一样,喜欢写诗,这冲抵了他对城市的陌生感。
正因为如此,袁叙田想着要为城市的80后诗人做点什么。2013年12月,由袁叙田主编的《深圳80后诗选》出版,收录了88位深圳80后诗人的186首诗。这本书出版后,深圳的80后诗人走得更近了,交流也更多了。
2016年,袁叙田与刘永一起主编了《向劳动致敬——我们的诗》,该书收录了在深圳较为活跃的100位劳动者诗人的近150首作品,后来成为当年读书月重点推荐的阅读书目,并参加了第26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来深圳后,袁叙田的工作有多番变动,先是在深圳地铁公司运营总部当工班长,后来跳槽到一家公司做品牌策划,再后来到面点王当了一名企业文化主管。去年底,他再次跳槽到一家影视公司,转型当起了编剧、导演。

▲袁叙田
生活动荡,而初心不改。或者说,他的一次次跳槽,也与诗歌写作训练给他带来市场议价能力的提升有一定关系。
70后李晃、80后袁叙田以及90后诗人刘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惠州跟人谈事情,电话里有点嘈杂——他们代表了深圳一个庞大的诗歌写作群体,构成了城市的诗歌基层。他们在城市奔波、在不同工作间迁徙,生存的压力、快节奏的生活,并不能消磨掉他们对诗的向往。
正如广东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杨克在为袁叙田与刘永主编的《向劳动致敬——我们的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
“广东的深圳、东莞和珠三角其他城市,是外来普通劳动者孕育和释放巨大社会潜能的重镇……他们涉猎不同的工种,身份尴尬,艰辛生存,甚至消殒了生命,写下了灿若繁星的诗作……他们在社会摸爬滚打中,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
版权声明:
本专栏刊载的所有内容,版权或许可使用权均属晶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复制或改动,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如需转载或使用,请联系晶报官方微信公号(jingbaosz)获得授权。
(原标题《元故事 285期 │ 深圳诗人群落》)
编辑 黄力雯 审读 韩绍俊 二审 张克 三审 周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