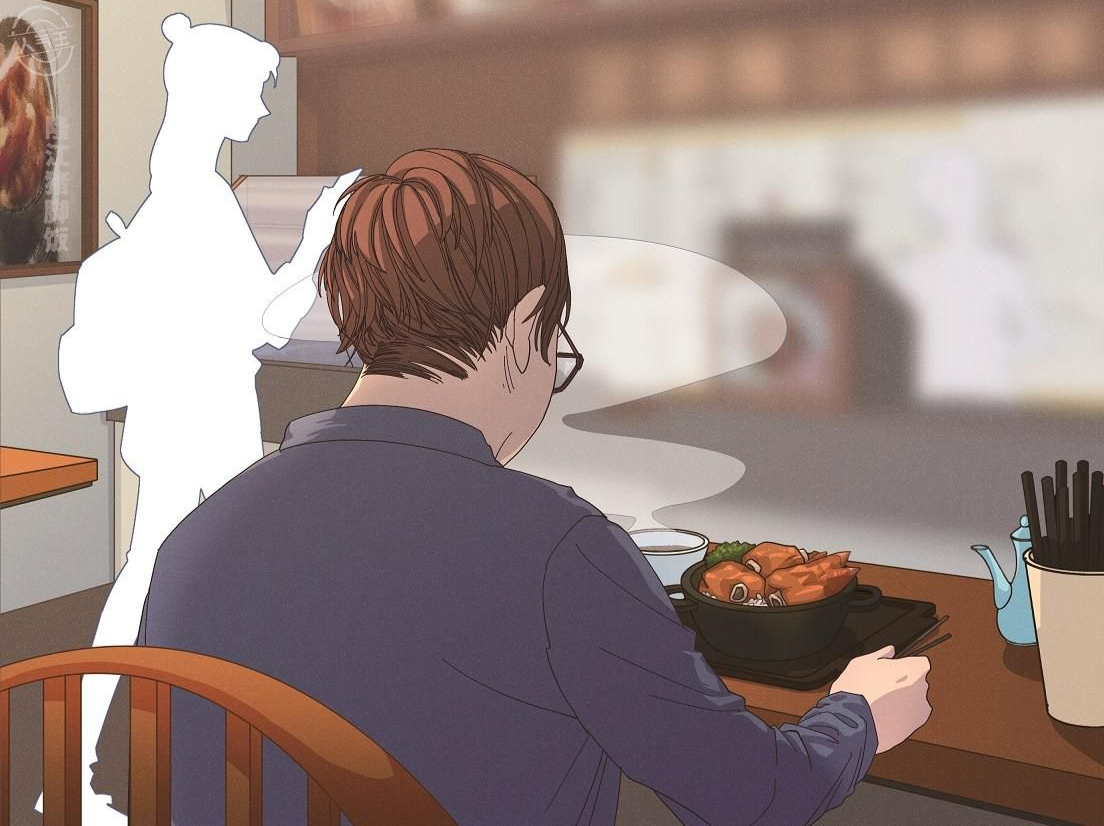2022年8月2日。
这天深圳依然高温,最高38℃。在树荫如盖的罗湖区东晓花园里,居民们一如平常。不同的是,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度夏方式——收获菠萝蜜。这和他们的欢乐一样,几乎不为外人所知。
作为一种热带水果,菠萝蜜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深圳不少小区都有种植。东晓花园不大,建有8栋住宅楼,伴有8棵菠萝蜜树。原籍湖北黄石的胡先生退休之后就住在这里。8月,正是菠萝蜜成熟的季节。这天临近中午,他借助一架梯子,轻快登上一人多高的树杈处。站稳之后,接过同伴递上的长杆,瞅准哪只菠萝蜜够大,就使劲捅过去。一声声闷响之后,一个个硕大如榴莲的菠萝蜜就落在了地上。
“你拿这只!小心白色胶汁!”“你拿那一只,那个饱满!”跳下树来的胡先生看着自己的战利品,与两位阿姨分配着。他特意交代:菠萝蜜拿回家后不能久放,两三天后稍稍放软就可以吃了。
幸运如我,同样获赠了一只菠萝蜜。
8月4日,当我将这一情景转述给正在大理避暑度假的刘佳胜时,他哈哈大笑。
如今年轻的深圳人并不一定知道,东晓花园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所在的8588平方米土地,恰是1987年12月1日“土地拍卖第一槌”所拍出的。主槌人正是刘佳胜——时任深圳市土地管理改革办公室主任,搭档则是会讲粤语、时任深圳市基建办综合处处长的廖永鉴。当时参加竞投并最后中标的,则是内地首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其负责人是骆锦星。
他们的名字与这块土地以及东晓花园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
刘佳胜祖籍江苏江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刚刚过完国庆节,即从广东省测绘局来到深圳,那一年35岁。1982年5月,刘佳胜第一次去了香港。“那时是走罗湖铁路桥而不是罗湖人行桥过去的,去之前还发了600元的服装费。”他说。
回首“土地拍卖第一槌”,刘佳胜说,这是一次重大改革。而改革需要强烈意识,以及知识、魄力和策略。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各种会上吵架——带着《资本论》与人吵。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土地是财富之母。‘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见《资本论》第三卷,第701页。”刘佳胜至今记得这个出处。“为什么土地革命战争时,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因为土地本身的价值,这个不能否认。”
当时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无疑给改革带来了压力。为此,酷爱读书的刘佳胜从《资本论》中找到了改革依据,并据理力争。
这是理论和舆论上的铺垫。而“土地拍卖第一槌”之所以能够落槌,在于彼时特区建设面临着现实压力,即所谓“形势比人强”。
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大面积铺开。对于市政府来说,一方面,用于“三通一平”的资金日增;另一方面,大量土地却是无偿划拨给几大开发企业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在召开外商座谈会时,得知香港来自土地的收入占到了香港财政的15%以上,当即要求组成房地产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土地管理改革办公室和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并组成房地产改革考察团,赴港考察香港相关制度。
刘佳胜正是考察团成员之一。1986年11月17日,考察团通过罗湖桥到达香港。
“这次考察一共10天,因为通行证只有7天,中间还往返了一次。我们考察了香港地政署、田土注册处以及银行、房地产商、中介机构等,加上大量购买阅读相关书籍和报刊,摸透了香港房地产行业的关键环节。正是在这次考察中,结识了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以及测量师梁振英等专业人士。他们见我们特别认真,是真想干事,因而没有保留倾囊相授。加上此前往返深港的积累,连台湾乃至新加坡的相关情况也掌握了。”
1986年12月28日,考察团即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提交了《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报告》。刘佳胜拟出了土地管理改革方案,一共三页纸,简明扼要。
但在那之后,推进速度慢了下来。这些都没有脱离李灏的视线。
1987年1月临近春节的一天,李灏在办公室听取了刘佳胜有关土地改革进展的专题汇报。刘佳胜先从经济学上作了一番阐述:一旦改革成功,将给政府财政、企业资产和个人财富带来根本性变化。对此李灏频频点头。但当他追问还有何难点何时落地时,刘佳胜面露难色。听了剖析之后,李灏没有吱声,他掏出一包“555”香烟,抽出来两支。就这样你一支我一支,不停抽起来,房间里的烟雾仿佛凝固起来。
十多分钟后,李灏目光炯炯,突然抛出一句话——
“如果要你坐牢,我去给你送饭,你干不干?”
“士为知己者死。”
刘佳胜语气铿锵。

▲拍卖会上的刘佳胜(左)。
二
之后,相关工作全面提速。
1987年2月,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上报深圳市委市政府。
5月,深圳市召开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论证会。
7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其主要内容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市场,使用者以平等竞争的市场形式(协议、招标、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合同规定期内,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可以转让、出租或抵押。
9月9日,深圳以定向议标的形式,将第一块地批租给中航工贸中心。这是第一种方式。
10月6日至9日,“国家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召开,重点围绕土地有偿使用的理论依据、土地制度改革与现行法律政策的关系、土地市场的建立、城市土地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土地政策与土地管理等问题进行研讨。
11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向国务院提交试点报告,被国务院批转。25日,深圳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将第二块地有偿转让给深圳市深华工程开发公司——这是第二种出让方式。
至此,以国际惯例即公开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已臻成熟。这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里的第三种方式——百分百的市场方式。
但即便如此,“土地拍卖”当时在深圳市政府文件中都表述为“土地竞投”,提前刊登的则是《土地竞投公告》,回避了“卖”这个字。
随着《土地竞投公告》的发布,竞投日一天天临近。竞投到底能不能成功?这块地能不能卖出去?作为直接负责人,这些问题一直压在刘佳胜心头。
11月的一天,深华工程开发公司经理文冲来到刘佳胜办公室,咨询有关竞投事宜。就在两人说话时,特发房地产公司副经理黄世滇也来了,表达有关诉求。
两人并不认识,心里想的都是那块地。黄世滇无意中就说了深华的“坏话”。如此一来,两人当场就吵了起来,且不可开交。刘佳胜一边劝架,一边恍然大悟:竞投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起码要有两个真正的买家。而大多数的,可能是看热闹的。
刘佳胜的心放下了:要让有诚意的买家都来竞投,这事就成功了大半。
三
竞投日很快到了。当天天气预报显示,阴天有分散小雨,最高12℃,最低5℃。但刘佳胜清楚记得,从市委大院走到深圳会堂的路上,没有下雨。
当天《深圳特区报》头版罕见对此作了预告性报道,且不再回避“卖”字——其主题是《市政府按国际惯例拍卖土地》,引题同样开宗明义——《土地按照商品属性进入市场》。在会堂里,“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首次公开拍卖”的横幅格外醒目。
此前的一天,刘佳胜还有些郁闷。因为在布置会场时,政府办公厅通知他,出席拍卖会的领导只有分管副市长。但在当天,新的通知来了,要他将深圳会堂前三排座位全部空出来。
拍卖会之前,刘佳胜专门去了香港两趟,现场观摩土地拍卖会——“看他们卖地,把他们卖地的词儿都记得烂熟”。得知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土地,刘绍钧和梁振英特意从英国定制了一只枣红色的樟木拍卖槌赠送给深圳。这只重2.95公斤的樟木拍卖槌上有铜牌,上书:“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 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 1987年12月1日”。拍卖会上,这只拍卖槌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
后来的拍卖过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在17分钟跌宕的拍卖中:起拍价为200万元,使用期为50年的H409-4宗地最后被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竞得——每平方米折合为611元。而参加竞投的经理骆锦星,与刘佳胜一样,都经过了香港房地产业的熏陶。早在1985年,他就参与过香港深水埗一块土地的竞投,战胜了长江实业、新鸿基等对手而夺标。这次是势在必得创造了历史。骆锦星一直引以为傲的是,他是叫价到400万元之后才举牌的。

▲拍卖会盛况空前。

▲深房以525万元竞得“第一拍”。 刘廷芳/摄
事实证明了刘佳胜的预想:市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深华工程开发公司和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都参与了400万元以上的竞投——是44家竞投企业中的诚意买家。只是在最后,深华才惜败于深房。
刘佳胜会后才知道,就在台下的前三排,当时除了李灏等市领导,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等领导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香港方面则派出了由刘绍钧带队、28人组成的“深圳第一次土地拍卖参观团”。这一场景,盛况空前。
1988年7月,由深房开发的东晓花园建成。今年88岁的骆锦星回忆说,当时市价每平方米接近2000元,但依照拍卖时的承诺利润不超过15%,每平方米售价约1600元,结果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
1987年出让的三块土地加起来,深圳市政府得到了2336.88万元的土地使用费,超过了特区1985、1986两年全部土地收入总和。
至于那只樟木槌,后来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是“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上的流量展品。
四
作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事件,“土地拍卖第一槌”的冲击波无与伦比。
在深圳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厦门、天津、上海等城市相继进行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试点。
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写道: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此,土地本身的价值以及土地之上的生产力被完全解放。
不过在刘佳胜看来,“土地拍卖第一槌”仅仅是个开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乃至深圳房地产市场的发端更加重要。
“土地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和资金、劳动力和技术一样,转化为生产力。土地无偿划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土地拍卖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体系。”1988年1月,刘佳胜被任命为深圳市国土局副局长(注:局长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深受《第三次浪潮》一书的启发,他从需要配套解决的八个问题入手,开启了土地管理制度的系统改革。
在土地拍卖之后,要发给开发商产权证。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开发商建成住房卖给企业或个人,同样要发房产证。这就是对产权的保护,没有法律保护,就没有市场交易,就没有房屋抵押,就没有市场经济。房地产中介机构就如同介绍所,可以活跃交易提升效率。唯有将整个管理体系建立起来,才能促进市场的发展。由此,房地产市场就形成了。本着这些理念,深圳国土部门在整合之后,其职能相当于内地5个部门之和,显著提升了行政效能。
至于土地供应计划的学问就更大,无论是土地供应还是住房供应,最重要的就要保持供需平衡,实行动态调整。这要结合人口规模、产业状况等综合决策。如果供需不平衡,要么土地价格畸高,要么土地卖不出去。深圳国土部门在处理计划和规划的关系以及依法行政等方面做了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如在规范卖地合同时,水电在什么地方接入,都有明晰的规定,这才能让企业算账和决策。而在办文办证方面,率先设置了办文办证时效规定。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办结,系统将自动警示,内设的行政监察处将进行问责。以按时办理房地产证为例,就充分体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有力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在刘佳胜看来,“土地拍卖第一槌”最大意义在于:深圳在土地使用权拍卖之后,成立土地开发基金,进行滚动开发。其模式复制到全国之后,产生了巨大的核裂变效应:这使地方政府有了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的资金来源,使得城市建设和运营有了滚动发展的动力。从最初的“三通一平”到后来的“七通一平”,没有土地拍卖,城市化以及房地产市场就无从开启。以1999年建成通车的滨海大道为例,每公里建造成本高达5亿元,总投资50亿元。通车之后,沿线乃至南山土地拍卖收入高达数百亿元。这是“土地拍卖第一槌”之于中国城市化以及房地产发展的最大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土地拍卖收入连续4年甚至超过财政收入,乃至于当时深圳市政府对国土局重奖1000万元。这一巨额奖励本身,就说明了深圳市政府对于土地拍卖价值的最高体认。深圳,率先“闯”出这一步不是偶然的。
以2021年为例,国内土地出让金总额达到了8.7万亿元,深圳土地出让金亦达1558亿元。8月4日,深圳进行了今年第二批14宗土地集中出让,合计收入339亿元。
从这一点来说,由东晓花园结出的“菠萝蜜”效应还在持续。

▲东晓花园“土地拍卖第一槌”纪念墙。
总建筑面积36860平方米、容积率为4.3的东晓花园目前市场价在5万元/平方米左右,总市值约18.4亿元——这便是当年所拍出的525万元所带来的巨变。随着周边小区城市更新的推进,已有34楼龄的东晓花园未来依然保有焕发第二春的可能。
8月6日晚,我在家剥开了那只带回来的菠萝蜜。
既香又糯,也甜。
(晶报记者李果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 周晓飒 许家宜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关越
(原标题《元故事 067 期│“第一槌”和它的菠萝蜜》)